今天我救人一命,算造了七级浮屠。早上楼梯口遇到一个同事,刚入职的女孩子,一边哭一边打电话叫出租车,一脸通红,还时不时用手按胸口,摸喉咙,我看不对,走过去问她发生啥了?她哭着说出不了气了,喉咙很痛,我一下就紧张起来。 早上七点半,写字楼楼梯间的声控灯忽明忽暗,我抱着刚买的豆浆油条往上走,三楼平台拐角撞见她——那个上周入职、工位在茶水间旁边的女孩子,扎着低马尾,白衬衫领口沾了点咖啡渍,正蹲在台阶上哭,手机贴在耳朵上,声音抖得像被风吹的纸片:“师傅…能不能快点…我快喘不上气了…” 她另一只手死死攥着胸口的衬衫,指节泛白,喉结上下滑动,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儿,每咽一下都抽口冷气。 我停下脚步,豆浆杯在手里晃了晃,热乎的液体蹭到虎口——平时在电梯里点头之交都算客气,这会儿该不该过去? 她突然抬头,眼睛红得像兔子,看见我,眼泪掉得更凶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完整的话,只是重复“喉咙…痛…出不了气…”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扔掉豆浆就冲过去:“别等出租车了!我送你去医院!” 她愣住的瞬间,我已经拉起她的手腕——皮肤烫得吓人,比刚出锅的油条还烫,腿软得像面条,几乎整个重量压在我胳膊上,嘴里还在嘟囔“我没钱打车…” 我吼她:“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塞进副驾时,她头靠在椅背上,眼睛闭着,胸口一起一伏得越来越慢,我突然慌了——万一我判断错了呢?万一只是她太紧张了呢? 可当我摸到她额头的冷汗,听见她喉咙里发出的“嘶嘶”声,踩油门的脚更狠了。 后来医生说,是急性喉头水肿,再晚半小时,窒息风险极大;而她手机里的打车记录显示,最近的出租车还堵在三公里外的早高峰里——原来所谓的“等一等”,有时候真的会变成“来不及”。 我为什么会冲过去?或许是她攥衬衫的动作太用力,像要把自己勒出一道印子;或许是楼梯间太安静,她的哭声混着电话里司机不耐烦的“堵车啊”,显得格外孤伶伶——我们都是这座城市里的孤岛,平时隔着工位隔板假装不熟,可真见着谁要沉下去了,总不能站在岸边看着吧? 那天下午她发微信给我,头像是只晒太阳的猫,说“谢谢你没让我变成新闻里的‘某写字楼年轻女子猝死’”。 我回了个笑脸,心里却在想,我们每天在格子间里算KPI、比业绩,可最该算的,或许是对身边人那一点点“多管闲事”的勇气——你看,就因为多问了一句“你怎么了”,一条命就这么被拽回来了。 晚上下班再走楼梯,声控灯亮了,台阶上还留着一小片干掉的泪痕,像谁不小心洒了滴墨水。 我想起她早上攥着我胳膊的力道,想起医院走廊里她递过来的、还带着余温的热牛奶——原来“七级浮屠”不是什么宏大的功德,就是某个普通的早上,你伸手拉了一个快要沉下去的人一把。
今天我救人一命,算造了七级浮屠。早上楼梯口遇到一个同事,刚入职的女孩子,一边哭一
小杰水滴
2025-12-14 09:26:32
0
阅读: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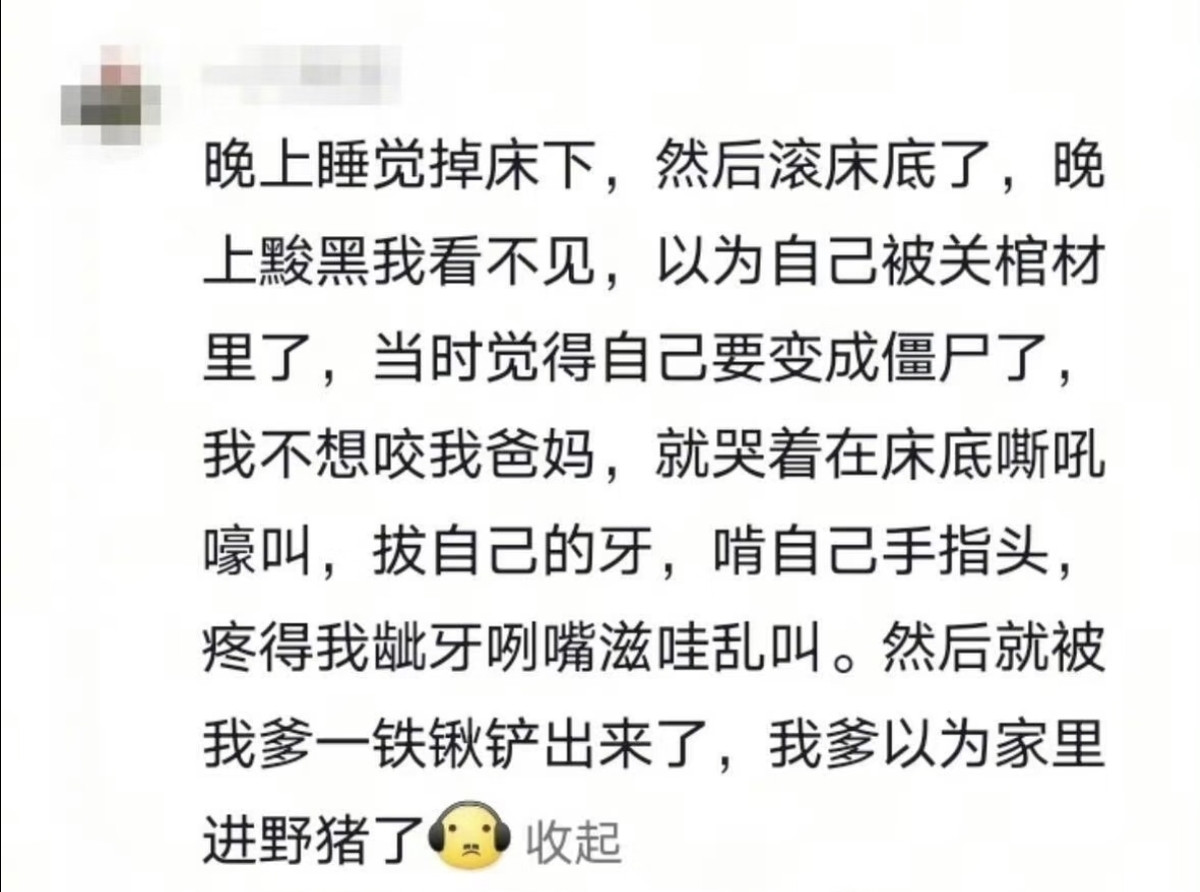


![女子学校偷外卖被做局吃到屎报警[笑着哭]因外卖多次在学校被偷又抓不到人,便想出](http://image.uczzd.cn/3842064799001999251.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