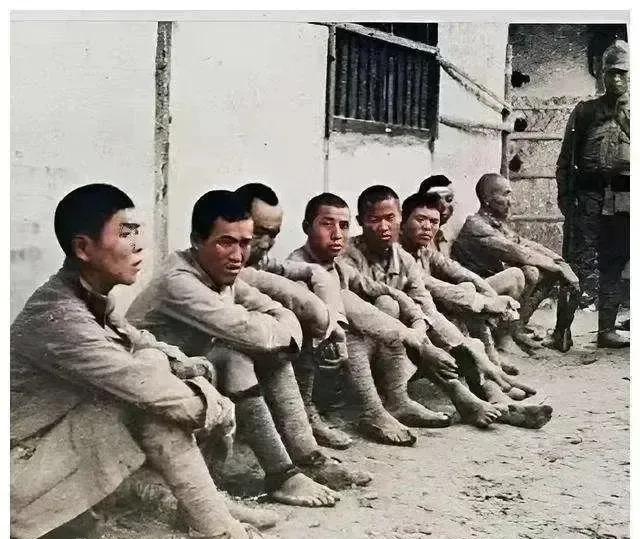1935年,13岁小红军罗玉琪过草地时突然腹痛不止,碍于女同志就跑远处去方便,不料返回后竟发现草地已空无一人…… 四下静得吓人。草地茫茫一片,半人高的草浪在风里晃着,刚才还有队伍嘈杂的人声、马蹄声,这会儿只剩下呜呜的风响。罗玉琪愣在原地,肚子还抽着疼,手心却冒了冷汗。她踮起脚往各个方向张望,除了望不到边的草甸和低垂的灰云,什么也没有。 队伍走了。红军大部队像被草地吞掉了一样。 她才十三岁,参加红军不过半年。当初跟着村里几个青年偷偷离家,一是想吃饱饭,二是因为听说红军是为穷苦人打仗的。母亲哭着塞给她两块烤土豆,她咬咬牙就跟着队伍进了川西。这一路枪林弹雨没掉队,翻雪山时脚冻烂了也撑着,没想到在这看似平静的草地上,竟因为肚子疼被落下了。 不能慌。她想起班长说过的话:“草地上掉队,九死一生。”可班长没教她,一个十三岁的女娃子掉队了该怎么办。 风越来越冷,草甸上的湿气漫上来,裹腿布早就湿透了。罗玉琪把腰间的草绳系紧些,那是她唯一像样的“腰带”。她蹲下来,仔细看泥地上的痕迹,杂乱的脚印朝着一个方向延伸,有些深有些浅,还有马蹄印子。脚印被踩倒的草正在慢慢挺起来,再不跟就真找不到了。 她拔腿就往那方向跑。草划过脸颊生疼,呼吸里全是草腥和土味儿。跑着跑着,眼泪不知不觉糊了一脸。不是怕死,是怕孤独。红军队伍就是她的家,没了队伍,她就像被丢进茫茫大海的一根草。 跑了大概半个时辰,脚印渐渐模糊了。前面出现一片水洼子,浑浊的水漫过草丛,看不清底下是泥还是坑。罗玉琪停下来喘气,突然听见隐约有人声。她心头一跳,赶紧伏低身子,拨开草缝往外看,不是红军,是几个穿着破羊皮袄的藏民,正牵着两头牦牛慢慢走过。 她想喊,又闭上了嘴。长征路上指导员反复交代:要团结少数民族,但不能随便暴露。她咬着嘴唇,眼看那几个人越走越远。 天暗下来了。草地上的天黑得特别快,刚才还能看见远山的轮廓,转眼就只剩灰蒙蒙的影子。罗玉琪又冷又饿,摸出怀里最后半块青稞饼,小心地啃了一小口。饼硬得像石头,嚼在嘴里全是麦麸的涩味。她舍不得吃完,重新包好塞回怀里。 夜里绝不能睡。班长讲过,草地上睡着就可能再也醒不来。她找了块稍干的草墩子坐下,抱着膝盖,瞪大眼睛盯着黑暗。远处有绿莹莹的光点飘忽——是狼,还是磷火?她攥紧了怀里唯一的“武器”:一把削过马草的小刀。 风穿过草甸的声音像无数人在低语。她忽然想起娘,想起离家前夜娘在油灯下补她的衣裳,线脚密密的。娘说:“跟着红军好好走,别回头。”她现在真的不能回头了。 后半夜下起了细雨。雨丝冰凉,钻进领口、袖口。罗玉琪把头上破旧的八角帽往下拉了拉,身子缩成一团。迷迷糊糊中,她好像听见了号声,猛地抬头。只有雨打草叶的沙沙声。 那是她一生中最长的一夜。 天蒙蒙亮时,她被一阵鸟叫声惊醒。浑身冻得发僵,手指都弯不拢。她挣扎着站起来,腿脚麻得针扎似的。得继续走。朝着昨天判断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 太阳出来了,草甸上升起白茫茫的雾气。走到一处稍高的坡地时,她忽然停住了——前方雾气散开的地方,隐隐约约有红旗在飘! 她揉了揉眼睛,生怕是幻觉。不是,真的是红旗,还有人影在动。罗玉琪想喊,嗓子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只发出嘶哑的“啊”声。她拼命朝那个方向挥手,拔腿狂奔,被草根绊倒了就爬起来接着跑。 越来越近了。她看见熟悉的灰色军装,看见挑着锅的炊事班老李,看见队伍末尾那个一瘸一拐的小战士,是跟她同村的豆子! “罗妹子!”有人喊她。 队伍停下来等她。她扑进人群里,几个女战士一把抱住她,冰凉的军装贴着脸,她却觉得暖和极了。指导员走过来,没批评她,只拍了拍她的肩:“回来就好。”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队伍遭遇了小股敌军袭扰,紧急转移了路线。大家以为她跟着另一支小队走了,直到清点人数才发现少了人。 很多年后,罗玉琪老人回忆这段往事,总是平静地说:“草地教了我一件事,革命的路,你得自己认准方向走。队伍可能会一时看不见,但旗杆在前头,你就不能停。” 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有多少像罗玉琪一样的少年少女,用他们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时代的重量?他们迷茫过、害怕过,却在最孤独的时刻依然朝着认定的方向前进。那不是神话,是一个个普通人在绝境中做出的不普通的选择。长征路上,每一个“不掉队”的身影,其实都是在用生命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而活,又为什么而坚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