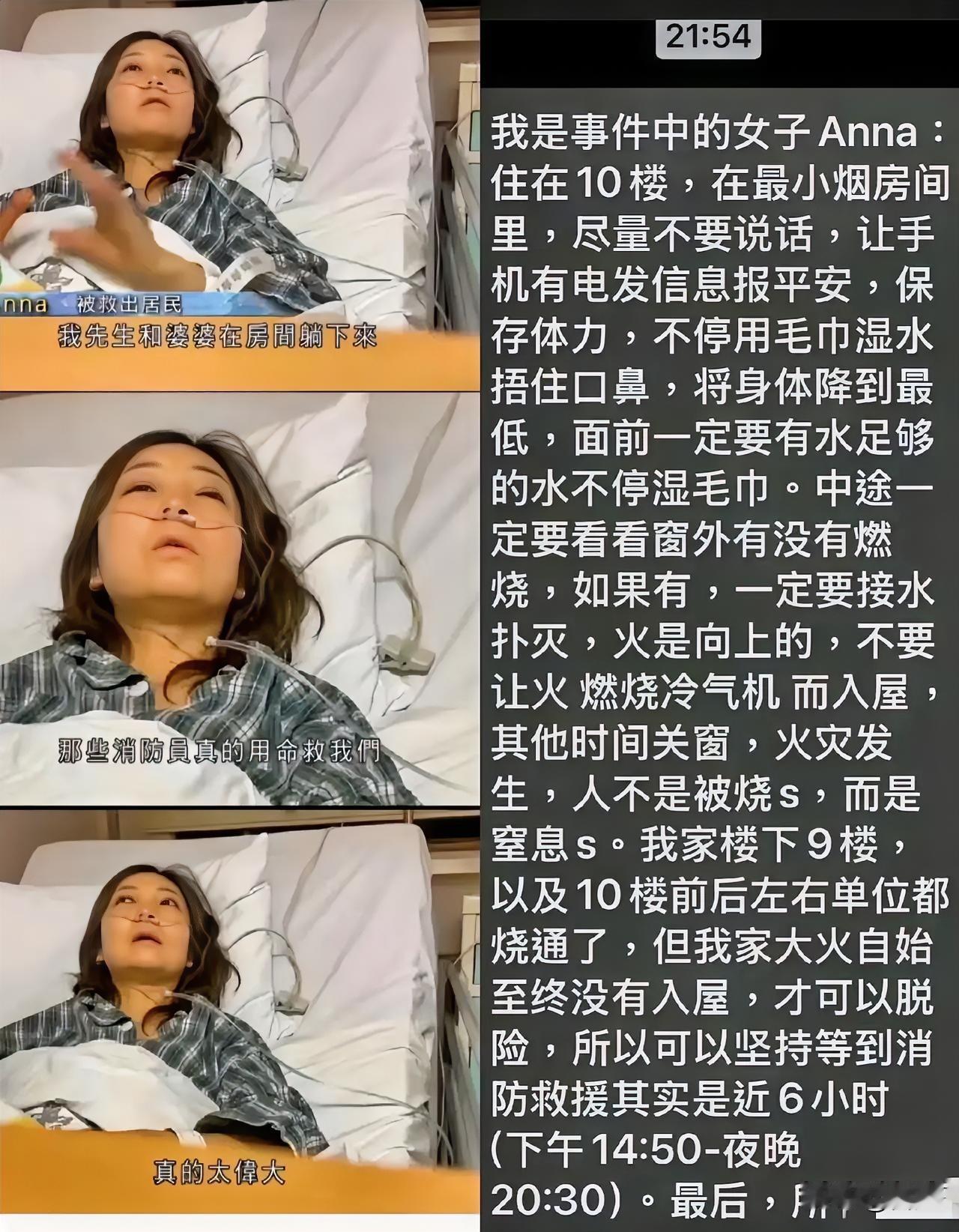我有个朋友经常去爬秦岭。他说,他遇到过一座尼姑庵,里面的尼姑都很瘦,因为没钱,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有一次爬山时,他拎了两小壶油和几斤橘子送给她们。那座庵藏在秦岭深处的一道峡谷里,没有路标,只有一条被踩得发亮的石板路通向那里,路两旁长满了带刺的酸枣树,朋友第一次误打误撞找到时,裤腿都被勾出了好几个洞。 我有个朋友,老李,人不算外向,唯独对秦岭有种执念——每个月总要空出两天,背个旧帆布包就往山里钻。 他说秦岭深处藏着太多故事,有的在石碑上,有的在山民的烟袋锅里,还有的藏在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角落里。 去年秋天他跟我讲起那座尼姑庵时,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包带上的划痕,那是被酸枣刺勾的,一道叠着一道,像串起来的省略号。 那天他本想抄近路翻海拔一千八的垭口,走着走着路就没了,只剩条青石板路往峡谷里钻,窄得刚够放下半只脚,两旁的酸枣树疯长,枝桠伸到路中间,针尖似的刺在阳光下闪着光。 他走了快一个钟头,裤腿被勾出好几个洞,膝盖也蹭破了皮,正想掉头,听见前头有若有若无的钟声——不是寺庙那种洪亮的,像用铜片轻轻敲出来的,闷闷的,裹着山雾飘过来。 拐过最后一道弯,看见几间灰瓦石墙的小房子,屋檐下挂着晒干的野菊花,门口坐着个穿青布僧衣的尼姑,正低头缝补一件打了补丁的僧袍,针脚密得像山里的苔藓。 老李说他当时站在原地没敢动,那尼姑抬头看见他,也没惊讶,就朝他笑了笑,问他是不是迷路了,声音轻得像风吹过竹叶。 他后来跟我说,当时心里直打鼓——人家会不会觉得他是来打扰的? 他摸了摸背包,早上出门时顺手装的两小壶菜籽油和几斤橘子还在,是前一天在山脚下的镇子买的,本想自己路上吃,那一刻突然觉得该留给她们。 他把东西递过去时,手有点抖,那尼姑接过橘子,指尖凉得像山泉水,说了声“阿弥陀佛”,又从屋里端出碗热水,碗边有个小豁口,水是温的,带着点野菊花的清苦。 我问他,她们每天只吃一顿饭,会不会觉得苦? 老李沉默了会儿,说他当时也这么想,直到看见庵堂门口那畦菜地,萝卜缨子绿得发亮,旁边摆着个豁口的陶罐,里面插着几支野百合——开得比城里花店的还精神。 他说可能我们觉得的苦,在她们那里是另一种活法,就像那条石板路,看着难走,踩上去却稳当,每一步都贴着山的脉络。 从那以后,他再去秦岭,背包里总会多装两样东西,有时是几斤米,有时是包盐,不是特意带的,路过镇子时看见,就顺手买了。 上个月他又去了,说尼姑庵的野菊花开得正好,那个缝衣服的尼姑还记得他,给他看新腌的野山椒,装在玻璃罐里,红得透亮。 他没问她们为什么住在这么深的山里,也没说自己每次来都要多绕两小时路走那条石板路——好像走一遍,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就被酸枣刺勾掉了似的。 后来我想,人有时候需要这样的相遇吧?不是为了改变什么,就只是看见——看见另一种生活,也看见自己心里那点还没被磨掉的热乎气。 前几天老李发了张照片给我,秦岭的雪刚化,石板路上还留着浅浅的脚印,路尽头的尼姑庵屋顶飘着缕青烟,像谁在宣纸上轻轻抹了一笔。 他说下次爬山喊我一起,我说行啊,就是不知道我的裤子,能不能扛住那些酸枣刺。
我有个朋友经常去爬秦岭。他说,他遇到过一座尼姑庵,里面的尼姑都很瘦,因为没钱,每
好小鱼
2025-12-01 18:48:45
0
阅读: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