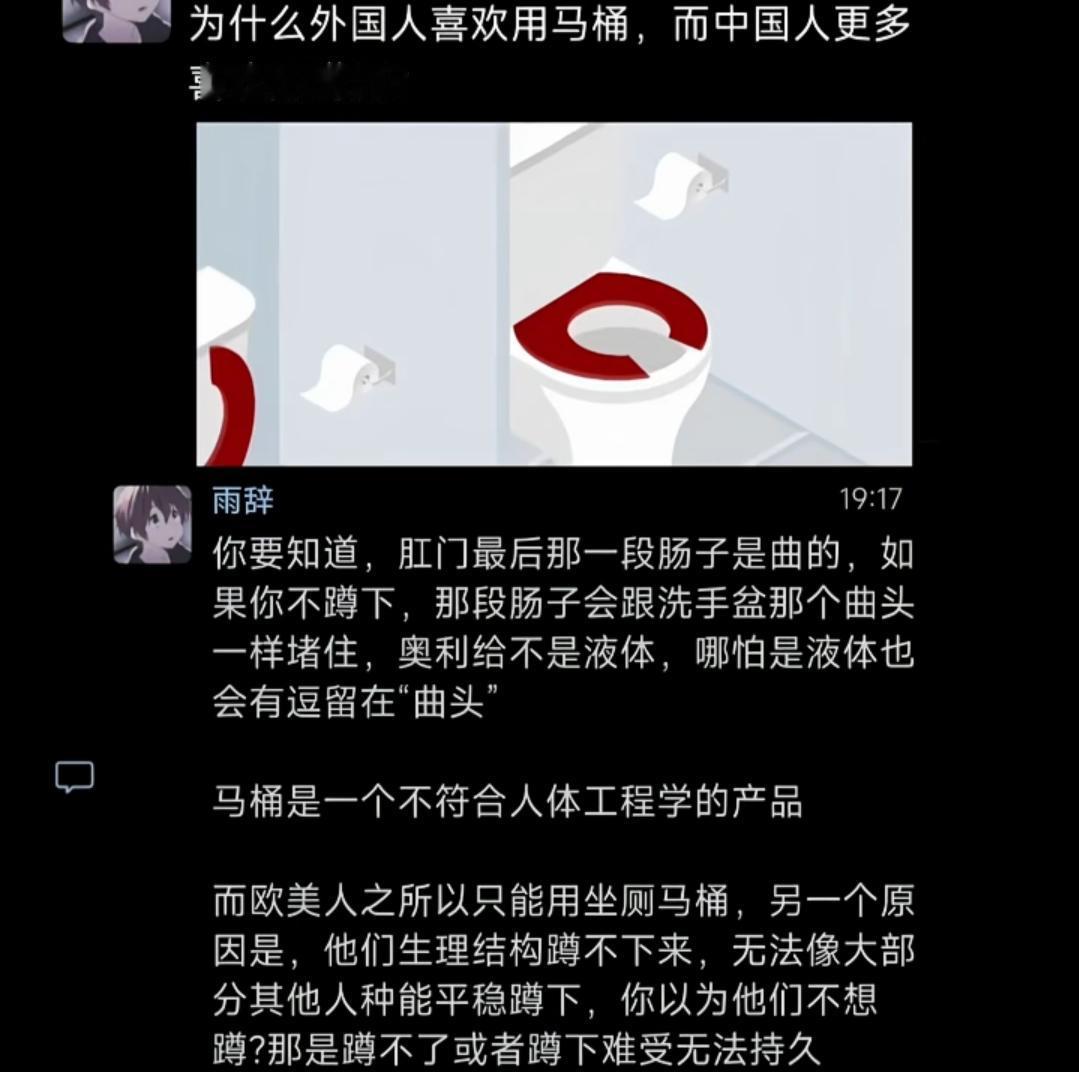1968年的台北,松江路那栋白色洋楼总飘着烤杏仁的香。 萧蔷的童年没见过“缺钱”长什么样,爸爸的贸易公司总往家里运新奇玩意儿,两个哥哥的书包里永远有给她留的进口糖。 红木梳妆台上摆着三哥从日本带回的樱花镜,她对着镜子涂口红时,妈妈总在门口笑:“我们蔷蔷以后要当电影明星哦。” 后来她真的走进了镜头,20岁拍丝袜广告,导演盯着监视器突然拍手:“这才是台湾最美的脸!” 报纸上开始叫她“台湾第一美女”,镁光灯追着她的高跟鞋,从颁奖台到富商云集的晚宴。 1998年那个秋夜,金冠酒店的宴会厅里,水晶灯把地板照得像撒了一地碎钻。 穿黑西装的富商端着酒杯走过来,手指上的钻戒晃得人眼晕,他凑到萧蔷耳边,声音黏糊糊的:“50万,陪我一晚,怎么样?” 周围有人假装看风景,服务生托着盘子的手顿了顿。 萧蔷正往嘴里送一小块提拉米苏,闻言慢慢抬起头,嘴角还沾着点奶油。 她没立刻说话,拿纸巾擦了擦嘴角,然后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富商的胸口。 “想睡我啊?”她眼睛弯成月牙,声音甜得像裹了蜜,“那得先给我当三个月奴才。” 富商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周围的抽气声比水晶灯还亮。 “每天给我提包、开车门、买早餐,少一次都不算数。”萧蔷转身时,香槟杯在手里转了个圈,“等你合格了,再谈别的。” 第二天报纸头条写“萧蔷耍大牌羞辱富商”,评论区骂声比点赞多。 有人说她“拜金又傲慢”,也有人翻出她和电子业大佬曹兴诚同游的照片,说“还不是靠男人上位”。 另一种解释是,她从18岁签第一份合约就没花过男人的钱,拍广告的酬劳够买三套房,和富商吃饭永远AA制。 曹兴诚送她的那栋阳明山别墅,她改成了流浪动物救助站,自己仍住在市区那套老公寓。 剧组里小演员道具坏了,她悄悄让助理去买新的,还叮嘱“别说我给的”。 那天被怼的富商后来再没出现在她的饭局,倒是有导演找她演泼辣角色:“就你这股子硬气,太合适了!” 四十岁后她渐渐少接戏,把更多时间耗在医院——不是打针医美,是给儿童病房捐绘本,给护士站送咖啡机。 有记者堵着问“怕不怕被新人比下去”,她正给孩子讲童话,头也不抬:“怕什么?她们还得练十年呢。” 现在她五十多了,偶尔在活动上见到当年的粉丝,对方还会红着眼喊“吟霜”——那是她三十年前演的角色名。 身材还像穿旗袍时那样挺括,只是眼角的细纹里,藏着比樱花镜更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