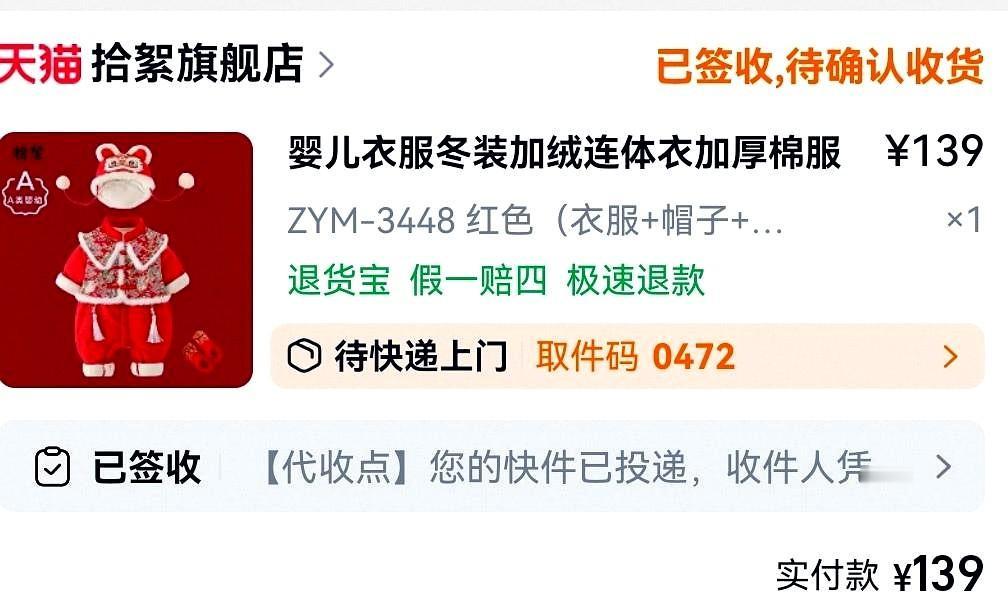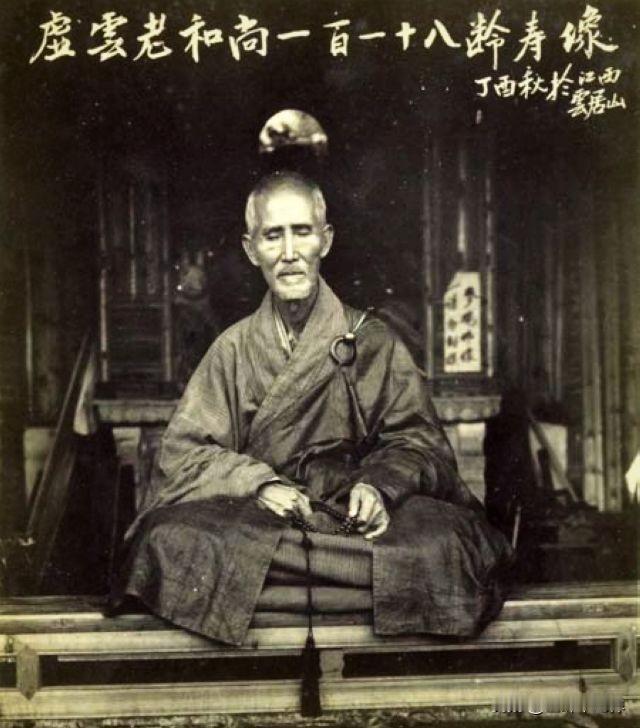1993年,6年没有收入的陈忠实在家闲坐。突然一通电话打来,接完电话后,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妻子吓得赶紧过来扶他,哪知,陈忠实却激动地说:“老婆,咱不用养鸡了!” 在西安灞桥区西蒋村,44岁的陈忠实坐在祖屋的竹椅上正在发呆。 这是他六年写作生涯里唯一的“奢侈品”。 突然,电话铃声炸响,他抓起听筒,编辑的声音从千里外传来:“《白鹿原》要出版了,版税按百分之十算。” 陈忠实双腿一软瘫坐在地。 妻子王翠英闻声冲进来,却见他笑出眼泪:“老婆,咱不用养鸡了!” 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西蒋村的土窑里。 塬坡下的几亩薄田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少年时他常饿着肚子上学,初中差点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多亏乡干部担保才读完。 1962年高中毕业,他回村当了民办教师。 1965年,他在《西安晚报》发了第一篇散文,稿费五块钱,给母亲买了半斤红糖。 1973年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刊出,他把样刊揣在怀里跑回家。 父亲摸着铅字说:“咱老陈家也出文化人了。” 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1982年调任陕西省作协专业作家,陈忠实和路遥、贾平凹并称“陕西文坛三驾马车”。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火遍全国,贾平凹的《浮躁》震动文坛。 他看着同行佳作,心里越来越难受:“中短篇写得再好,也立不住脚,得有部长篇才算本事。” 44岁那年,他拍了桌子:“不写出硬货,没脸在文坛混!” 决心写长篇的陈忠实,做的第一件事是辞职。 1986年冬天,他搬回西蒋村祖屋,把作协的办公桌换成土炕,对着墙上“垫棺作枕”四个大字发狠:“要么成,要么死。” 为写《白鹿原》,他先当“田野调查员”。 两年间,他搭班车跑遍蓝田、长安的县城,抄了几十卷县志,在田间地头和老农唠嗑,记了三大本民间秘史。 白鹿原上的祠堂规矩、族长轶事、妇女哭坟的调子,全往本子上扒。 1988年,他在土炕上铺开稿纸,写下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笔尖落下,四年伏案生涯就此开始。 六年没稿费,家里全靠王翠英撑着。 她白天种地、养鸡,晚上纳鞋底卖钱,省下的工资寄给丈夫当笔墨钱。 陈忠实心疼她,说:“要是书出不来,我就回乡下养鸡,咱不靠笔杆子吃饭。” 他甚至订了8万只鸡苗。 这是给失败的“兜底方案”。 1992年,五十万字手稿写完。 陈忠实用麻绳捆好,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高贤均。 编辑上门取稿时,看见屋里除了一张破桌、几 把竹椅,就剩墙角的啤酒瓶。 “这地方能写出好书?” 编辑捏着鼻子感叹,却把稿子小心翼翼抱上车。 等待出版的日子,陈忠实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每天去村口等邮差,见着骑自行车的就问“有信没”。 夜里睡不着,就数房梁上的蜘蛛网:“又没消息。” 妻子劝他:“急啥?好饭不怕晚。” 他嘴上应着,却已经开始准备着鸡苗订单。 1993年,邮差终于在晌午蹬着车进村。 陈忠实接过信,手抖得拆不开封。 等看清“同意出版”四个字,电话铃就响了,是编辑打来确认稿酬方式。 他不懂“版税”是啥,只说“能出书就行”,挂了电话就瘫在竹椅上。 王翠英冲进来时,他正捶着大腿笑:“老婆,咱不用养鸡了!书要出了,还给版税!” 那一刻,六年寒窑苦熬、妻子鬓角的白发、鸡苗订单上的红印章,全化作了滚烫的泪。 1993年6月,《白鹿原》首印1.5万册,三个月加印七次,总量超50万。 北京王府井书店排起长队,大学生抱着书在路灯下读到天亮,连偏远县城的书摊都挂出“陈忠实签名本”的牌子。 1997年,小说获茅盾文学奖,评委评价“写尽关中五十年变迁,是中国农村的《红楼梦》”。 改编的秦腔、话剧、电影、电视剧轮番上演,北京人艺的《白鹿原》连演百场,观众哭着喊“田小娥太苦了”。 发行量突破160万册,译成日、韩、法等语种。 陈忠实甚至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版税收入超455万。 可他没飘。 拿了钱先给村里修路,给母校买图书,自己仍住西蒋村的土窑。 晚年动手术瘦得脱相,还坚持练毛笔字,说“字是人的脸,不能丢”。 2016年4月29日,他因舌癌去世,73岁,枕的还是那本《白鹿原》。 陈忠实常说:“《白鹿原》不是我写的,是关中塬上的风、老农的烟袋锅子、女人的哭坟调,一起帮我写的。” 书里白嘉轩的腰杆、鹿子霖的算计、田小娥的挣扎,全是他从泥土里刨出来的“活人”。 如今,西蒋村的土窑成了“陈忠实故居”,每年有上万读者来打卡。 真正的“翻身”,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是用汗水泡透的坚持,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狠劲儿。 就像陈忠实说的:“好饭不怕晚,只要锅里有米,火候到了,自然香。” 主要信源:(光明日报——陈忠实在《光明日报》上的足迹 湖南日报——陈忠实:生命历程里的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