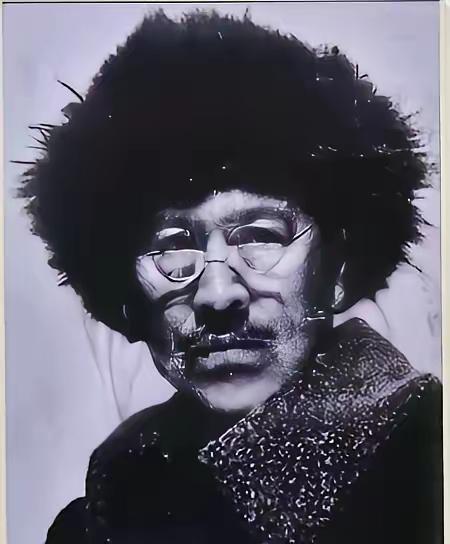1939年,白求恩被埋葬在河北唐县,由于他在前线战死,交通队只能秘密地把白求恩的尸体伪装成一个重伤的人,然后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1939年的深秋,河北唐县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生疼。交通队的王队长裹紧了破军装,看着担架上盖着的棉被,喉结滚了又滚——那下面躺着的,是白求恩大夫。 三天前,在摩天岭前线的临时手术室里,白求恩为了抢时间给伤员取弹片,手指被划破了。谁都没当回事,他自己也摆摆手说“小伤”,继续站在手术台边,一站就是三十多个小时。直到第四天,他的胳膊肿得像发面馒头,高烧烧得迷迷糊糊,才被战士们硬抬下手术台。可那会儿,败血症已经攥紧了他的命。 “不能让白大夫就这么埋在前线。”军区首长红着眼圈交代,“鬼子最近在扫荡,得把他送到后方于家寨,好好安葬。” 王队长心里清楚,这趟路险得很。从摩天岭到于家寨,一百多里地,一半是鬼子的封锁线,白天走就是自投罗网。他们只能等天黑,还得把白大夫的遗体藏好——要是被鬼子发现,指不定会干出什么缺德事。 入夜后,交通队员们把白求恩的遗体轻轻抬上担架,盖上厚厚的棉被,又在外面罩了件缴获的日军大衣。王队长让人找来个破草帽,戴在“伤员”头上,帽檐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脸。“记住,就说抬的是个重伤的老乡,要去后方治伤。”他压低声音嘱咐,手里的匣子枪上了膛。 队伍刚出村子,就遇上了麻烦。村口的老槐树下,两个伪军正缩着脖子烤火,看见担架就喊:“站住!抬的啥人?” 王队长心里一紧,脸上却堆着笑迎上去:“老总,是俺们村的一个老乡,被炮弹皮炸伤了,急着送后方救命,您行行好……”他偷偷往伪军手里塞了两个刚烤好的红薯,那是从老百姓家里讨来的。 伪军捏了捏红薯,热乎劲儿烫得手发麻,掀开棉被角瞅了一眼——白大褂的袖子露在外面,上面还沾着暗红的血。“快滚快滚,别耽误老子烤火。”他们挥挥手,眼睛早黏在红薯上了。 队伍不敢耽搁,借着月光往山里钻。担架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王队长总觉得担架太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他想起第一次见白求恩的样子:高鼻梁,蓝眼睛,操着生硬的中文喊“同志”,给伤员换药时,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瓷娃娃。有次村里的小孩得了急病,他背着药箱跑了十里地,鞋都跑掉了一只。 “白大夫,咱快到了。”王队长对着担架念叨,“到了于家寨,给您找块背风向阳的地,让您能瞅见咱八路军打胜仗。” 后半夜过封锁沟时,意外还是来了。巡逻的鬼子用探照灯扫过来,光柱像毒蛇似的在山路上舔。“快!躲进沟里!”王队长喊着,和队员们一起把担架抬进路边的土沟,用枯草盖得严严实实。 鬼子的皮靴声越来越近,王队长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摸着怀里的手榴弹,心想万一被发现,就拉响了跟鬼子同归于尽,绝不能让他们碰白大夫一根头发。 好在探照灯晃了晃就移开了,鬼子骂骂咧咧地走远了。队员们扒开枯草,发现棉被被树枝勾破了个小口,露出了白求恩那双没来得及换的皮鞋。王队长赶紧把破口掖好,眼眶热得厉害——这双鞋,还是去年冬天,延安的同志给白大夫捎来的,他总说“留给伤员穿”,自己舍不得穿,没想到最后穿在了这趟路上。 天快亮时,队伍终于赶到了于家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早有乡亲们等着,手里捧着刚从地里刨的新土。当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掀开棉被,露出白求恩安详的脸,人群里响起压抑的哭声。 “白大夫给俺家柱子治过腿,”一个老大娘抹着眼泪,“他说‘军民是一家’,这话俺记一辈子。” 安葬那天,没有墓碑,乡亲们就在坟头栽了棵松树。王队长对着松树敬了个礼,心里想:白大夫,您看,这地方多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有咱老百姓给您守着。 后来,有人说,那棵松树长得特别快,一年就蹿高了一大截。于家寨的孩子们常围着松树转圈,听老人讲那个蓝眼睛的大夫的故事——他从老远的加拿大来,把命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就因为他说“这里的人民需要我”。 很多年后,王队长再回于家寨,看见松树已经长得枝繁叶茂,树下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白求恩同志之墓”。他摸着石碑,像摸着当年那床盖在担架上的棉被,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比封锁线更坚固,比黑夜更长久。就像白求恩,他没留下啥值钱物件,可老百姓心里,早为他立了块永不褪色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