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野兔成灾,有100多亿只,体重百斤却无人食用,当地人给出答案:不敢吃。 时间要拨回到1859年,当时一位名叫托马斯·奥斯汀的英国绅士,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拥有一片牧场,为了满足狩猎的爱好,他从英国带来了24只野兔,放养在自己的庄园中。 他的初衷很简单:“没有猎物的乡村太无聊。”他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似无害的爱好,却成为澳大利亚生态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人为干预。 澳大利亚的气候温暖,野兔天敌稀少,食物丰富,这些“小可爱”很快适应了新环境,短短几十年野兔从几十只繁衍到了数亿只,成群结队穿越草原,啃噬庄稼,破坏植被,甚至让一些原生物种濒临灭绝。 到了21世纪,这场“兔灾”已经不再是生态问题那么简单,它成了一个令政府头疼、令农民崩溃的全国性灾难。 在南澳大利亚的一个偏远农场上,63岁的农场主比尔·托马森已经不记得他杀死过多少只兔子了,他说:“他们晚上成群结队地从林子里冲出来,像幽灵一样,吃光我种的麦子和蔬菜。” 比尔家的土地曾经年产小麦上百吨,现在却连40吨都保不住,每年为了防兔子,他要花掉近两万澳元来建围栏、买毒饵、请猎人,可没用,兔子总能找到缝隙钻进来,啃光一切。 虽然常见的野兔一般体重只有2-3公斤,但在某些地区,由于缺乏天敌、食物充足、基因突变等多重因素,一些野兔的体型已远超常规。 曾有捕猎者在新南威尔士州郊外捕获一只体长超过1米、体重接近50公斤的巨兔,照片传到网上,引发热议:“这兔子不是宠物,是怪物。” 巨型野兔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生态失衡的结果,它们食量巨大,破坏力更强,繁殖能力依旧惊人,一只雌兔一年能产5窝,每窝平均6-8只,而这些后代在4个月后就能开始繁殖。 “这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兔肉。”在墨尔本一家野生动物研究所工作的生物学家西蒙·卡特直言不讳地说道,“澳大利亚野兔携带大量寄生虫,体内毒素含量高,而且常年生活在农药残留严重的区域。” 澳大利亚曾在上世纪50年代试图用“粘液瘤病毒”控制野兔数量,这种病毒在兔子之间传播迅速,能在几天内杀死感染者,虽然短期内有效,但随着时间推移,病毒逐渐失效,兔子产生了抗性,但问题是这种病毒依旧在部分兔群中残留。 “你不知道你抓的那只兔子是不是‘带毒’的。”西蒙说,“而且它们身上常年携带跳蚤、蜱虫和多种线虫,对人类健康非常危险。” 此外澳大利亚对野生动物的屠宰和销售监管极严,想把野兔端上餐桌,你得通过多重检疫流程,成本高得离谱,甚至不如进口牛肉实惠。 澳大利亚政府对野兔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它们是生态公害,官方每年投入数千万澳元用于控制兔群数量,另一方面因为野兔数量巨大,处理方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更大的生态灾难。 曾有地方政府尝试用“激光围栏”驱赶野兔,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疫苗,用“生物绝育”技术抑制繁殖,但效果都不理想,兔子太聪明了,适应能力太强,几乎没有哪种手段能长期有效。 有声音说既然澳大利亚人不吃野兔,为何不出口给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法国等国家对兔肉的接受度较高。 然而野兔的“野性”决定了它不适合商业出口,首先它们在野外奔跑、啃食农作物,肉质粗糙、膻味重,与养殖兔完全不同;其次出口食品必须通过严格的检疫流程,野兔几乎全军覆没。 从一位英国绅士的随手放生,到如今的生态噩梦,澳大利亚的兔灾故事几乎成了人类干预自然的经典反面教材。 100多亿只野兔在澳洲大地上奔跑,看似是一场“动物乐园”的盛宴,实则是生态系统最深处的悲鸣。人类想要控制它们,却又束手无策;想要利用它们,又心生恐惧,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也远远看不到尽头。 而澳大利亚人那句“我们不敢吃”,不是因为兔子不可口,而是他们明白,眼前这些毛茸茸的动物,已经不是食物那么简单:它象征着一个被人为操纵、彻底失控的自然世界。 参考资料: 澳大利亚任命首任“野兔总管” 2025-01-12 鲁中晨报 兔子不光吃窝边草: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生物入侵事件 2023-07-26 北青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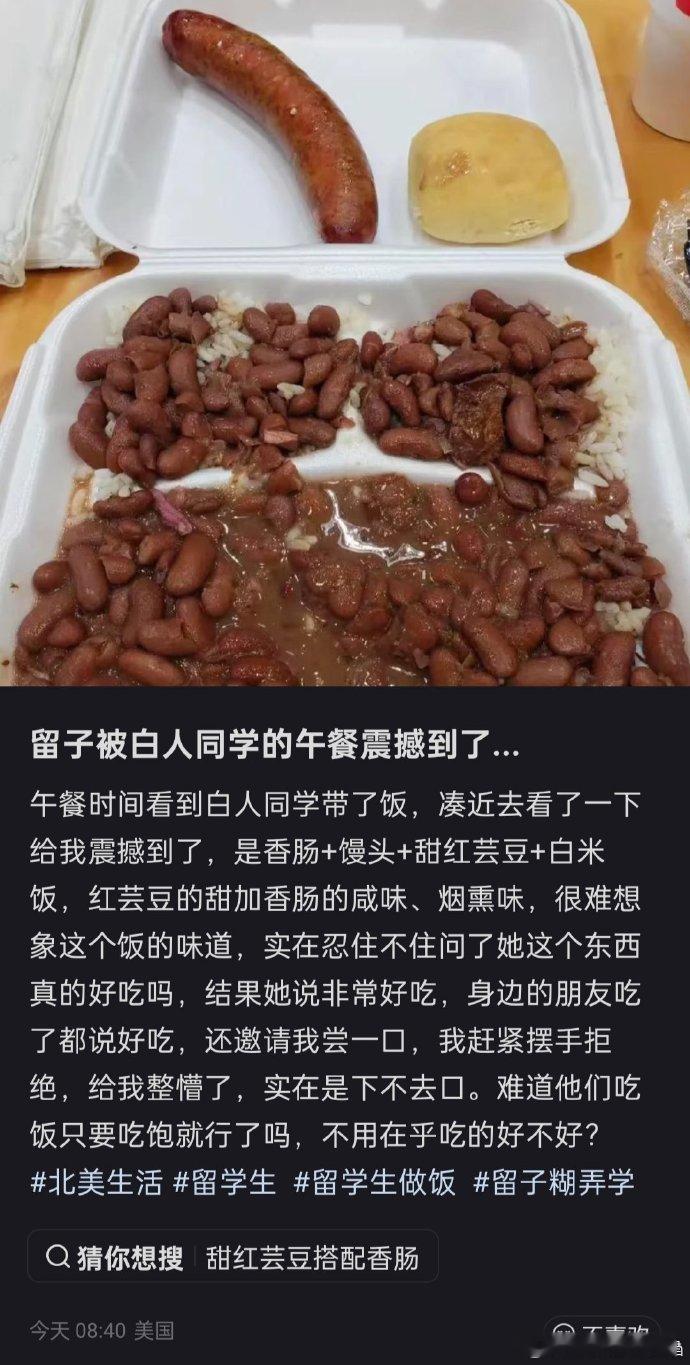





![当年不仅仅印度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吃瓜]](http://image.uczzd.cn/1709006580043240372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