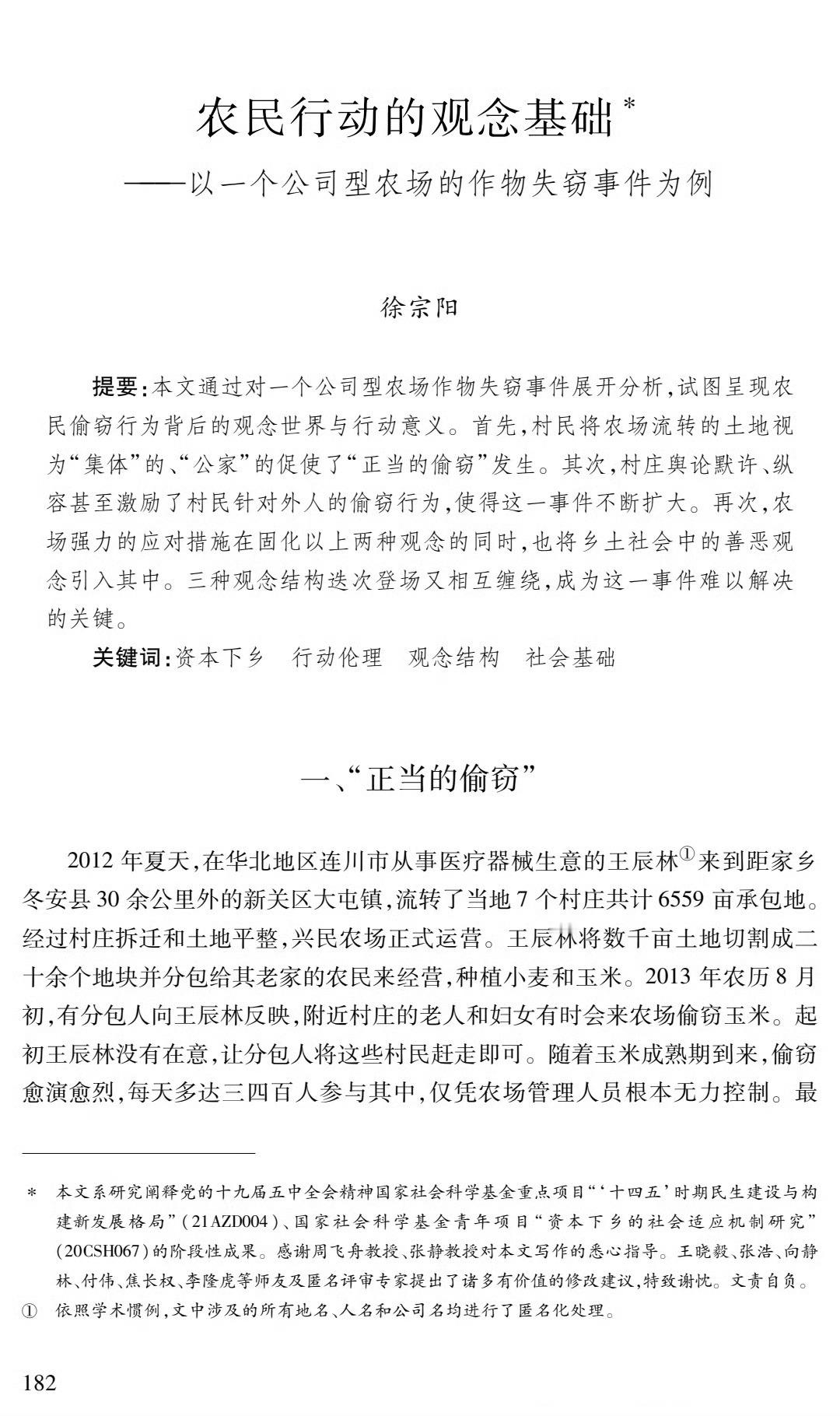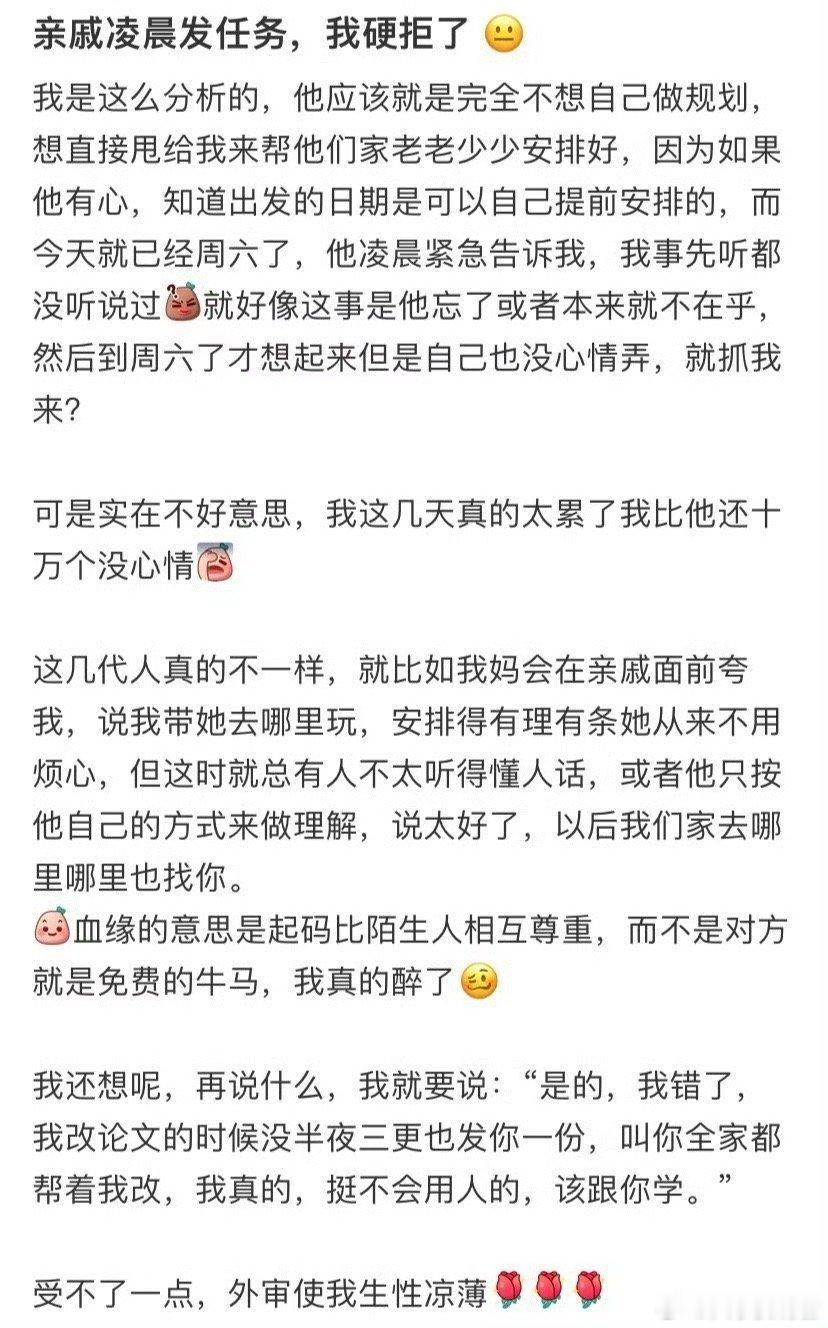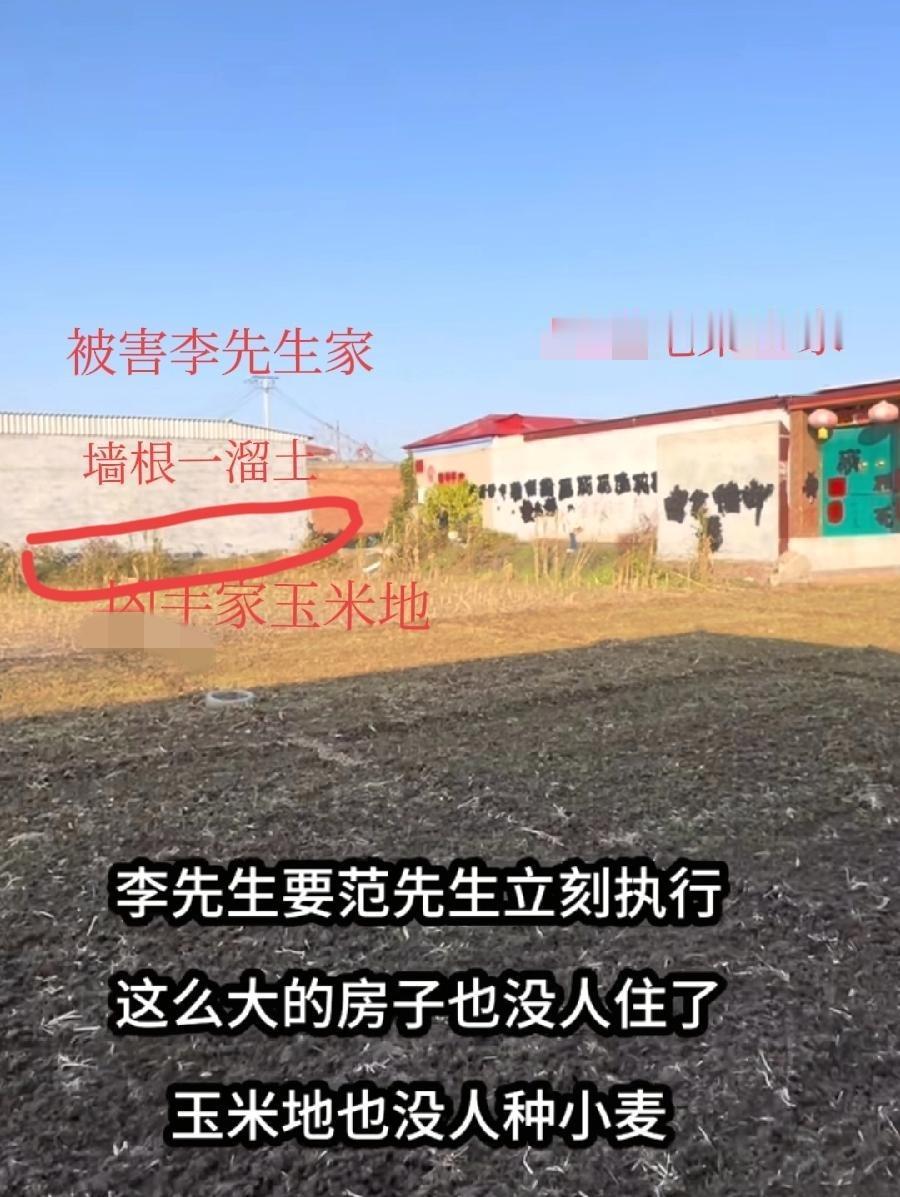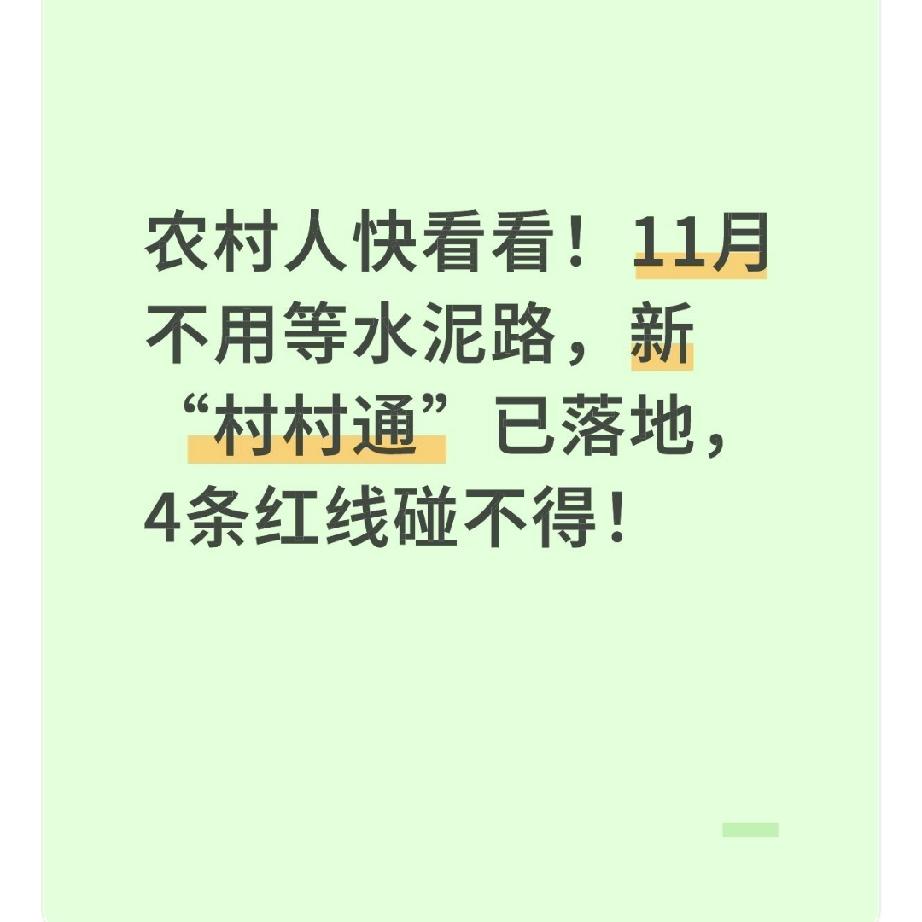一次次看到这种新闻,更一遍遍觉得这是好论文!写在了大地上。¹大老板去农村包地,靠拉电网、挖河沟、养藏獒、雇人看地都收效甚微。一般有效的做法是雇佣当地人,让当地人因为包地而收益。但总体上不是一个地方如此,普遍性都偷,所以怎么解释农民的这种“公开行窃”、他们自认为“正当的偷窃”才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²先说一个真实案例:2012年,华北某地有一个做医疗器械生意发家的生意人,他到距离老家30公里的一个镇,通过镇政府,快速流转了当地7个村庄,总共6559亩的承包地。他搞了一个大农场,主要种小麦和玉米。然而,仅仅到了第2年8月就出问题。附近十来个村庄的人偷他。主要是老人和妇女,有时候年轻人也来偷。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最多的时候一天三四百人来偷玉米。当然,他们自己不叫“偷”,叫“拿”,或其他土语,总之不叫“偷”。因为是流转的第1年,当地镇政府前后组织了600多人帮他日夜轮班看玉米。镇上的公安也出动,抓过多个偷盗数量比较大的村民,罚款、拘留。但收效甚微。当年700多亩玉米被偷,直接经济损失70多万。第2年、第3年、第4年,一直被偷。十来个村庄,骑着电动自行车、开着三轮车,甚至小型汽车来偷。没有固定的组织者,村民多为单独行动,心照不宣,不约而同。社会学研究者去采访,当地村民理直气壮,认为这是正当的。研究者采访正在偷玉米的年轻两口子,男的说他媳妇怀孕了,就想吃鲜玉米,没处买去,所以就来这里拉一车。理由五花八门。农场主甚至雇佣了一些能打人的年轻人,日夜巡逻;这些人跟当地村民起了肢体冲突。结果,当地村民更加认定这些人是“坏人”,于是偷地反而更加充满正义。那些被罚款,被抓去拘留的村民,回到自己的村子之后,他的朋友们甚至给他摆酒压压惊。这些人并没有因为偷窃而在道德上被同村人瞧不起。³怎么解释这些现象?作者徐宗阳开动社会学的脑筋,给出了三个原因的解释:第一,本来这些地都是村民自己的,但当地镇政府为了快速完成流转的任务,动了很多脑筋,迅速地把土地流转过来,再承包给外人。以集体的名义充公,于是激活了一个观念上的“集体”。历史记忆中,那几十年的集体生活下的“规则”,让村民们认为去掰农场的玉米,就是拿“公家”的东西。公家的东西在过去几十年是可以拿的,那么现在也是可以拿。第二,村民只“拿”这个农场土地上生长的玉米,对隔壁其他土地上的玉米秋毫不犯。因为那些土地的主人是“熟悉”的“自己人”,不是“外人”。拿外人的东西,被民间的舆论所默许、支持甚至激励;这里面存在一种扩大机制,表现之一:谁拿的多,谁最有本事。第三,当农场的“外人”反抗的时候,反而给自己带来又一个头衔:“坏人”。这里面是一种固化机制,村民们更加认为“拿”坏人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作者由此认为:¹农民在面对外来者时,会先界定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产生一种对应的行动伦理,再根据关系背后的原则与之相处。²同时,“当他们在眼前世界中无从判断外来者的位置时,会转而从个体经历或集体记忆中找寻。那么,我们就将深刻观察到宏观的农村社会变迁在农民身上留下的印记。”³费孝通老先生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写道: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这个故事有意思。因为比那些“农民就是自私”、“贪小便宜”等等负性道德评价的解释度更高;也能指出跟农民沟通、农村改革的一些方向。⁴回到“祁厅长”的例子。a,“祁厅长”被视为“全剧被杀死的2个农民的儿子”中的一个,是“自己人”,而且很照顾“自己人”,“村里的狗都想办法弄到城里当警犬,吃上一份皇粮”,所以农民在看待他时,评价的道德伦理便不同。b,“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反抗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领导者,但其效果不容小觑”。亦即,农民作为“弱者”,通过“弱者的武器”诸如偷盗、纵火、暗中破坏、支持“反行为者”等等,来与那些从他们身上榨取价值的人做阶级斗争。“反行为者”,指的是“处于压力之下的弱者,以表面顺从的姿态,自下而上地获得反制的位势,以求弥补损失,维护个人利益”。显然,给整自己的高阶层“梁老师”下跪等等的“祁厅长”,就是一个“反行为者”。先顺从,再反抗,极端维护个人利益。也因此,“农民的行动改变或减少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⁵有什么办法来改善这些呢?面对一个仍然深深根植于传统伦理本位的农村社会结构与人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