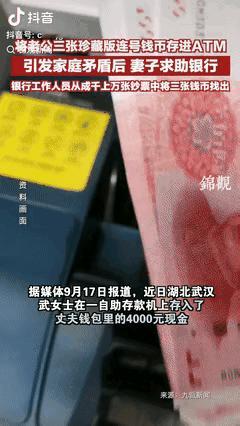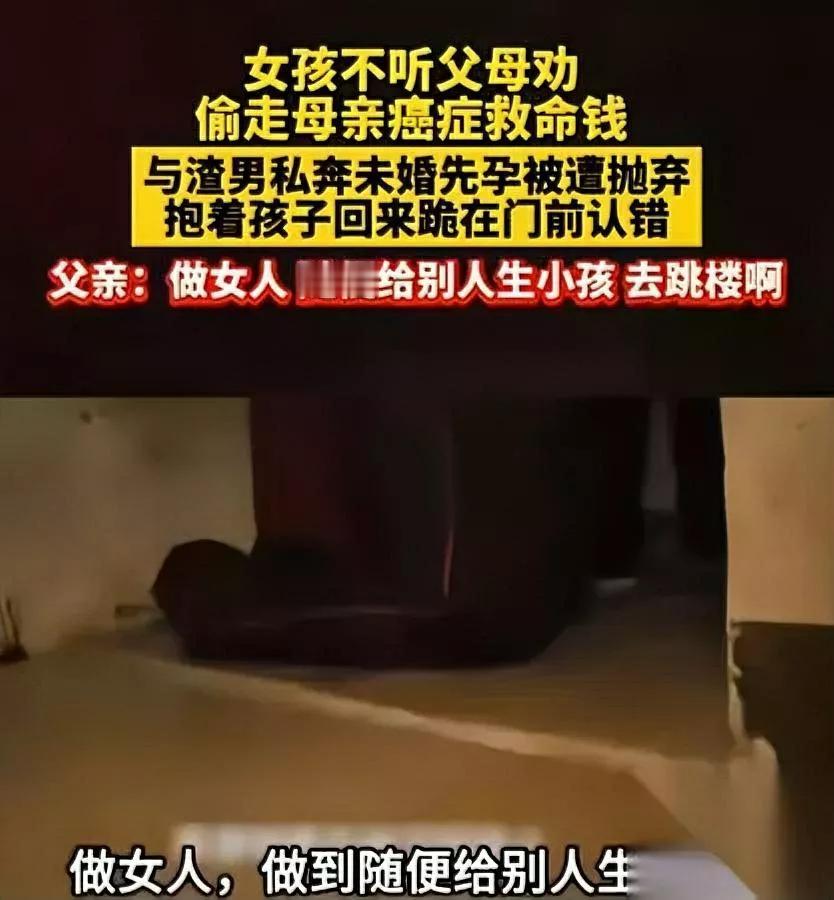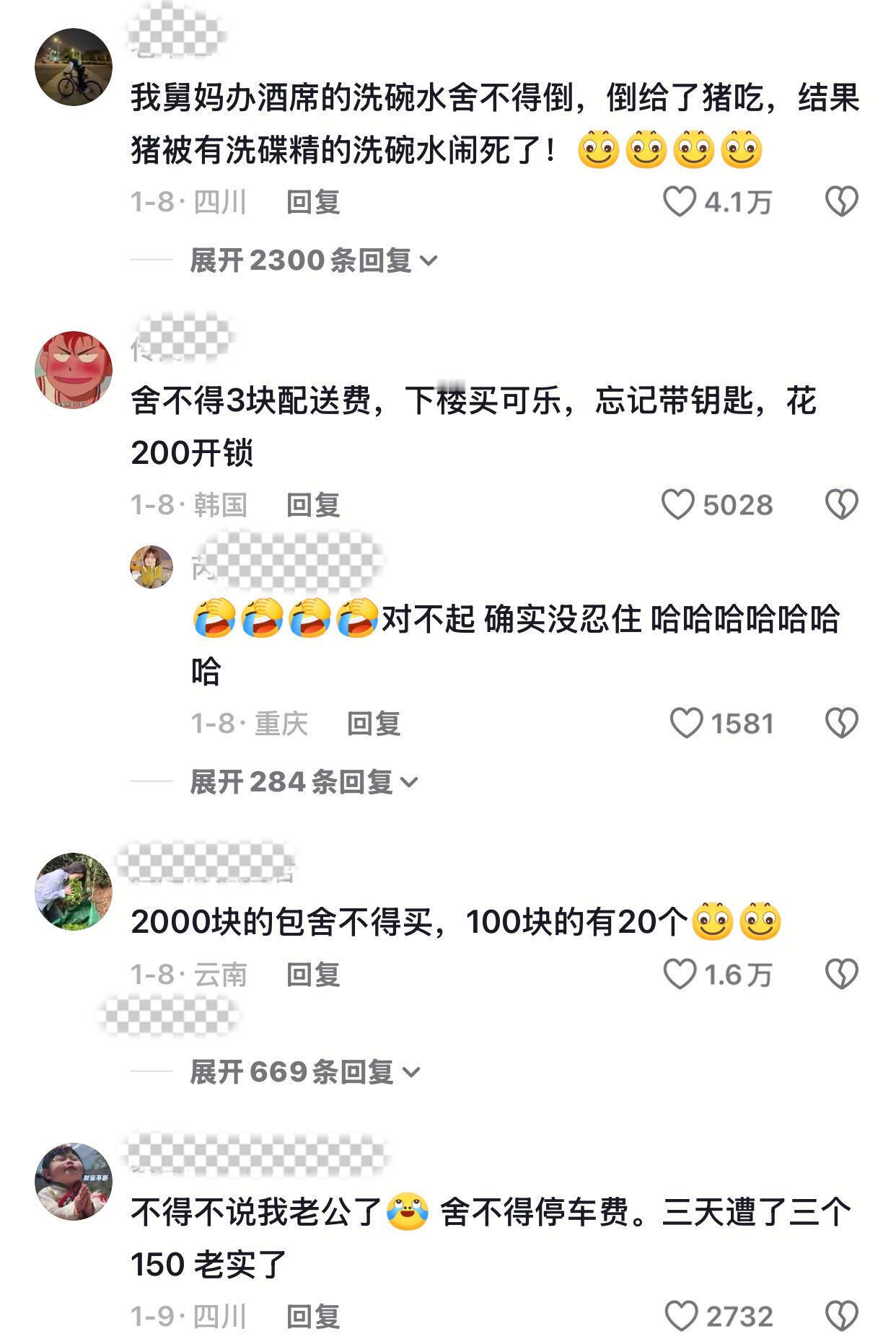1998年,大学教授何家庆来到深山调研,由于过于饥饿,于是就向村民讨吃的,不料村民居然端来一碗猪食,谁知这碗饭,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98年的一个深秋傍晚,何家庆拖着步子走进西南一处偏僻山村,他已经两天没正经吃过东西,身上背着的布包沉甸甸,里面是扶贫资料、标本和笔记。 饥饿让他眼前发黑,他敲开村屋的木门,低声请求些吃食,村民端来一碗掺了谷糠和野草的苞米糊,盛在缺角的粗瓷碗里,这本是猪食。 何家庆接过碗,蹲在门槛边,双手颤抖着将糊糊送进嘴里,粗涩的颗粒刮过喉咙,泪水从眼角滑下,他没有嫌弃,这一碗饭成了他此后一生的火种。 他出生在1949年的安庆,母亲早逝,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八口人,家里唯一的木床冬天漏风,他常挤在母亲身边瑟缩取暖。 少年时翻垃圾堆、捡煤渣补贴家用,鞋子破了靠同学送来旧鞋凑合,助学金、邻里凑的钱,让他跌跌撞撞读完了中学。 1960年考上安徽大学,学费全是乡亲们一分一角凑的,父亲用烟盒纸写下一句“要对得起人民”,攥在他手里,他心里烙下誓言:别人给一捧土,他要还一座山。 毕业后他留校教书,讲台上放着植物标本,他钻研大别山的植物资源,发现中国人竟没完整记录过那片山林,法国人在1910年采走五百余种,中国的学者却没有家底。 他不甘心,工资只有几十块,几年不添新衣,咸菜配馍硬是攒下三千元,父亲又从木盒里倒出一堆零票子,全是汗水和心血。 他背上帆布袋走进大别山,三百多座山,成千上万份标本,他走得脚底溃烂,衣服成了破布条,半年后他带出的报告惊动高层,国家批示推广,知识不应只是书本,他渐渐明白,山里人缺的不是力气而是科学。 九十年代,他被派去绩溪县担任科技副县长,骑着破自行车钻山沟,衣服补丁摞补丁,两年间他摸遍山林,办过野草展览,让农民认识脚边的植物。 推广魔芋时自己贴钱买种子试种,丰收那年几百户人家挣到第一桶金,离任那天,乡亲们堵住去路,送来一面写着“焦裕禄式好干部”的锦旗,他心里却压着更沉重的念头,西南的山沟比大别山还苦,他迟早要去。 1998年春天,他留下书信把全家积蓄两万七千元揣在怀里,背上布包出发,这是一场孤身的西行,跨越八省一百多个县,三万多公里的行程,其中八千公里靠双腿丈量。 山路险恶,鞋底磨穿十几双,血泡一层层叠在脚板,他被抢过两次,损失四千元,还被矿主逼去砸石头,手掌磨得血肉模糊。 他病倒在草垛上,村民杀掉下蛋的老母鸡熬汤给他;他在田埂上讲魔芋种植,嗓子嘶哑,汗水湿透衣衫。 三百多天,他走过四百多个村寨,办了两百多场培训,手把手教会两万多农民种植魔芋,还帮五十多家加工厂落地。 魔芋在他眼里不仅是植物,更是一条命运的出路,耐贫瘠,易加工,市场广阔,他发现魔芋的分布和贫困县高度重合,于是把精力全部扑上去。 每一次田间记录、每一次蹲地比对,都是在为农民寻找脱贫的钥匙,那碗粗粝的猪食,让他切身感受到贫困的极限,也让他更加坚信:让农民吃饱吃好,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 305天的西行结束,他回到合肥,体重只剩四十公斤,眼镜用竹片绑着,他挑着两筐标本站在车站,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女儿开门见他骨瘦如柴,布包磨出窟窿。 此后他依然不改初心,捐出奖金帮助儿童读书,继续研究瓜蒌,出版《中国栝楼》,跑遍十七个省份,拿到专利却无偿传授,他把知识当作农民手里的铁锄,能开出粮食和希望。 2019年夏天,他在潜山调研时晕倒,确诊癌症晚期,病床上报告纸散落枕边,他仍在写最后的调研,10月19日,何家庆走完了七十年的人生,留下捐赠的眼角膜,保存于眼库,送到山区孩子的眼中。 他的笔记、标本,成了安徽大学的遗产,大别山的药材林,绩溪的魔芋田,西南山沟里新盖的楼房,都是他生命的印记。 那碗粗糙的饭食,曾经是他眼泪中的苦涩,也是他一生的光,它让一个知识分子把脚步扎进泥土,让一个大学教授用瘦削的身影撑起无数农民的希望,别人给过他一捧土,他真的还回了一座山。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央广网——一本日记 走近“布衣教授”何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