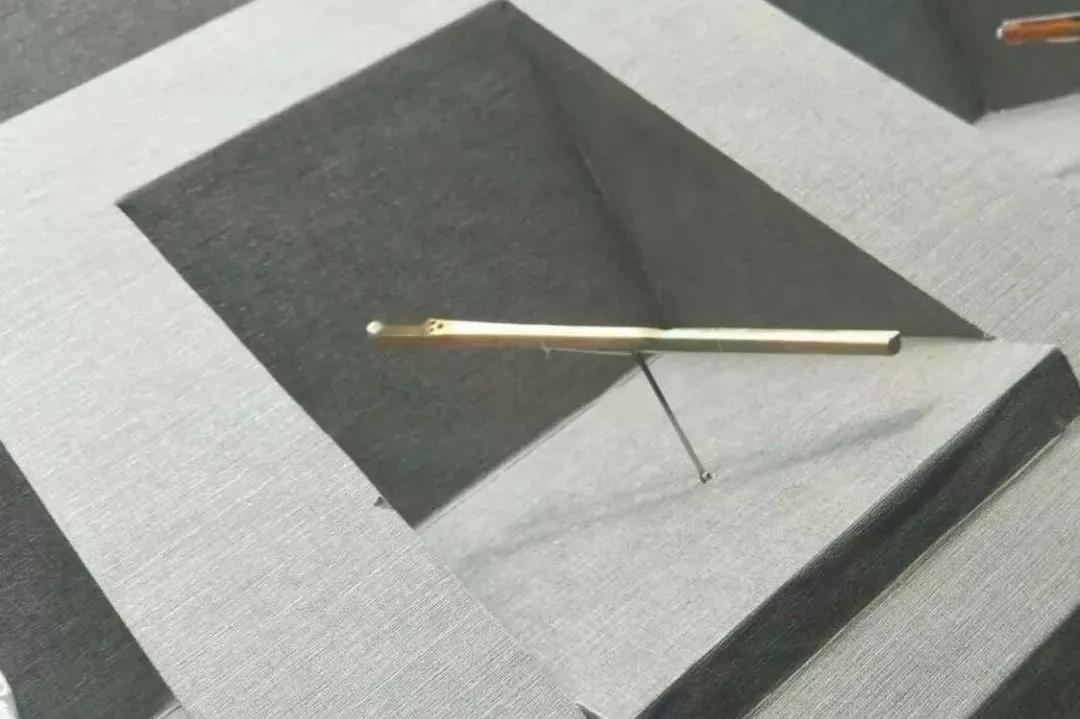这次回村特意走于家过道,却见家家大门紧闭、死气沉沉,没了往日热闹景象。青砖墙上爬满枯黄的藤蔓,风一吹簌簌往下掉碎屑。记忆里王大爷总坐在门槛上编竹筐,李婶端着洗衣盆在井台边说笑,如今连犬吠声都听不见。我站在老槐树下,树影斑驳地投在石板路上,当年几个孩子用粉笔画的跳房子格子,早被青苔盖得没了踪影。 路过二柱家,院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院子里荒草长得比人高,窗玻璃碎了两块,用塑料布胡乱挡着。正发愣,隔壁张奶奶颤巍巍地探出头:“是你啊,二柱一家早搬走了,去城里给孙子带孩子。” 她拄着拐杖走过来,指甲缝里还沾着泥:“这院子荒了三年,钥匙都不知道扔哪了。” “张奶奶,您身子还好?”我赶紧上前扶她,她手背上的老年斑像晒焦的枯叶。 “好啥呀,老胳膊老腿的,走两步就喘。”她往自家院门歪了歪头,“进来坐会儿不?院里晒着倭瓜干呢。” 我跟着她进了院,她家倒比二柱家齐整些,只是墙皮也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的黄土。屋檐下挂着串干辣椒,红得发黑,还有个旧竹篮,底儿都快烂穿了。 “村里咋这么静?我记得以前这时候,满街都是孩子跑。”我摸了摸院角那棵老石榴树,树干上还有小时候刻的歪歪扭扭的“王”字。 “都走啦。”张奶奶坐在门槛上,从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抖出根旱烟卷,“东头老刘家,儿子在深圳开出租,前年把老两口接走了;西院三婶,儿媳妇生了双胞胎,她去北京带孩子,说城里楼高,电梯都不会按;就连老支书,去年冬天走的,儿子把骨灰抱走,房子锁了,钥匙给了我,让我帮着看看。” 她划火柴的手直哆嗦,火苗舔着烟卷,“就剩咱几个老的,走不动,也不想走。守着这老房子,就跟守着念想似的。” 我想起小时候,张奶奶总端着碗玉米糊糊站在门口喊我,碗里卧着个金黄的荷包蛋。那时候她家灶台总冒着热气,蒸笼里的白面馒头能香一条街。 “您吃饭咋整?”我瞅见她家厨房门虚掩着,想进去看看。 “瞎对付呗。”她摆摆手,“村头李老头隔三差五给送点菜,自己再煮点粥。前天想蒸个馒头,面都发不起来,老了,手也笨了。” 我心里有点发酸,蹲下来帮她把散落在脚边的倭瓜干捡到簸箕里。这倭瓜干晒得皱巴巴的,跟她脸上的皱纹似的。 “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她忽然问,眼睛亮了亮。 “就今天,下午就得走,城里还有事。”我声音有点低。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只是一口一口抽着旱烟,烟圈慢悠悠地飘起来,被风一吹就散了。 坐了没多大会儿,太阳开始偏西,把树影拉得老长。我起身要走,张奶奶从屋里颤巍巍抱出个布袋子:“这是今年新晒的红薯干,你拿着,路上吃。” 袋子有点沉,我捏了捏,红薯干硬邦邦的,想必是晒了很久。 “您留着自己吃。”我推回去。 “我牙口不好,咬不动。”她硬塞到我手里,“拿着吧,好歹是奶奶的心意。” 我没法再推,只好接过来。袋子上还沾着点灶灰,带着股烟火气。 走到村口,我回头望了望。于家过道还是老样子,只是更安静了,只有风吹过枯藤的“沙沙”声。张奶奶还站在门口望着我,瘦小的身影像棵被风刮弯的老玉米。 车子发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慢慢转过身,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回院子,顺手关上了那扇掉漆的木门。 袋子里的红薯干硌得手心有点疼,我捏了一块放进嘴里,甜丝丝的,就是有点硬,得慢慢嚼。嚼着嚼着,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村子,好像真的老了。
我家住8楼,我楼上的楼上(10楼)刚搬来一家农村人,让我特别反感!我没有看不起
【48评论】【14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