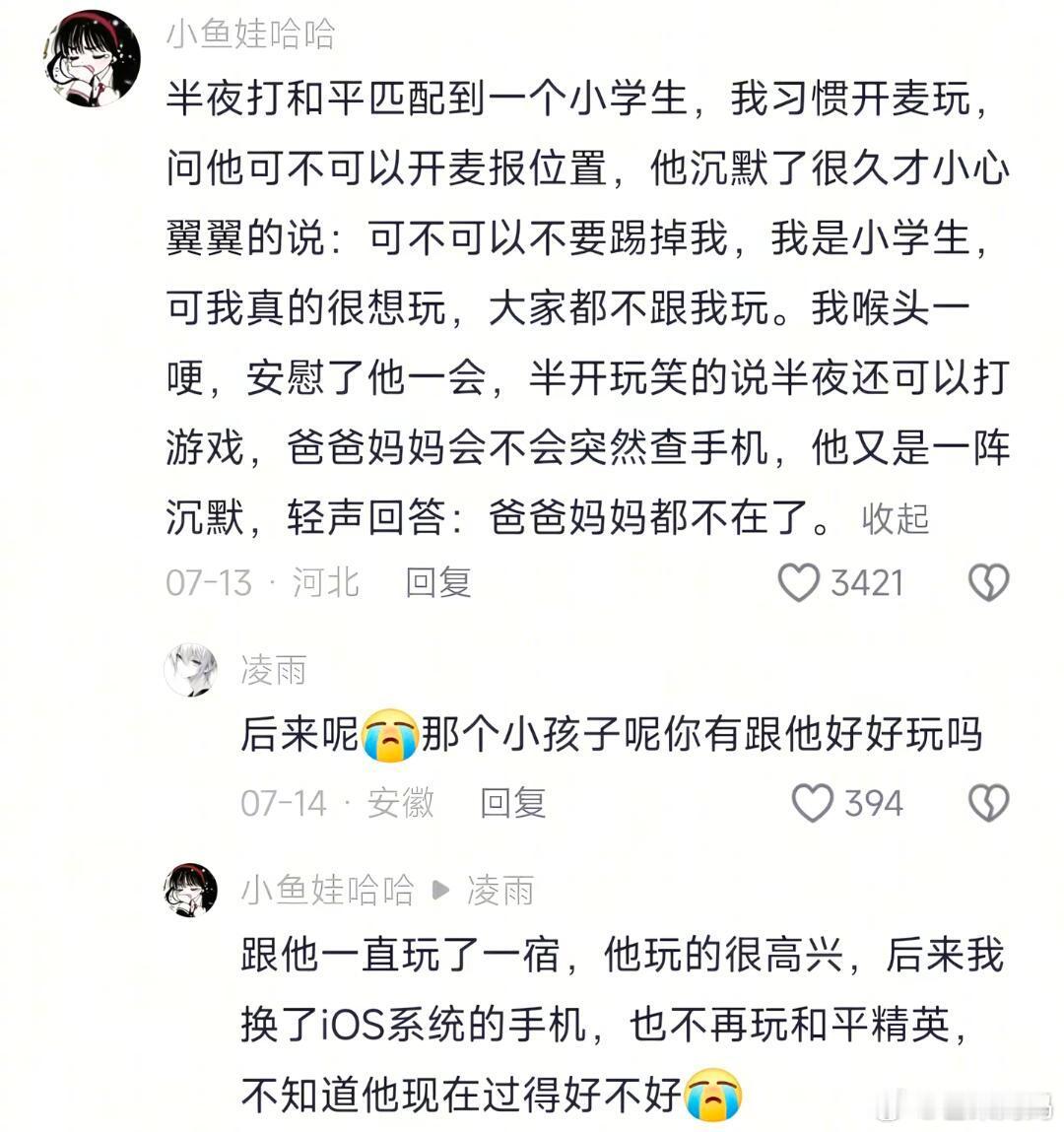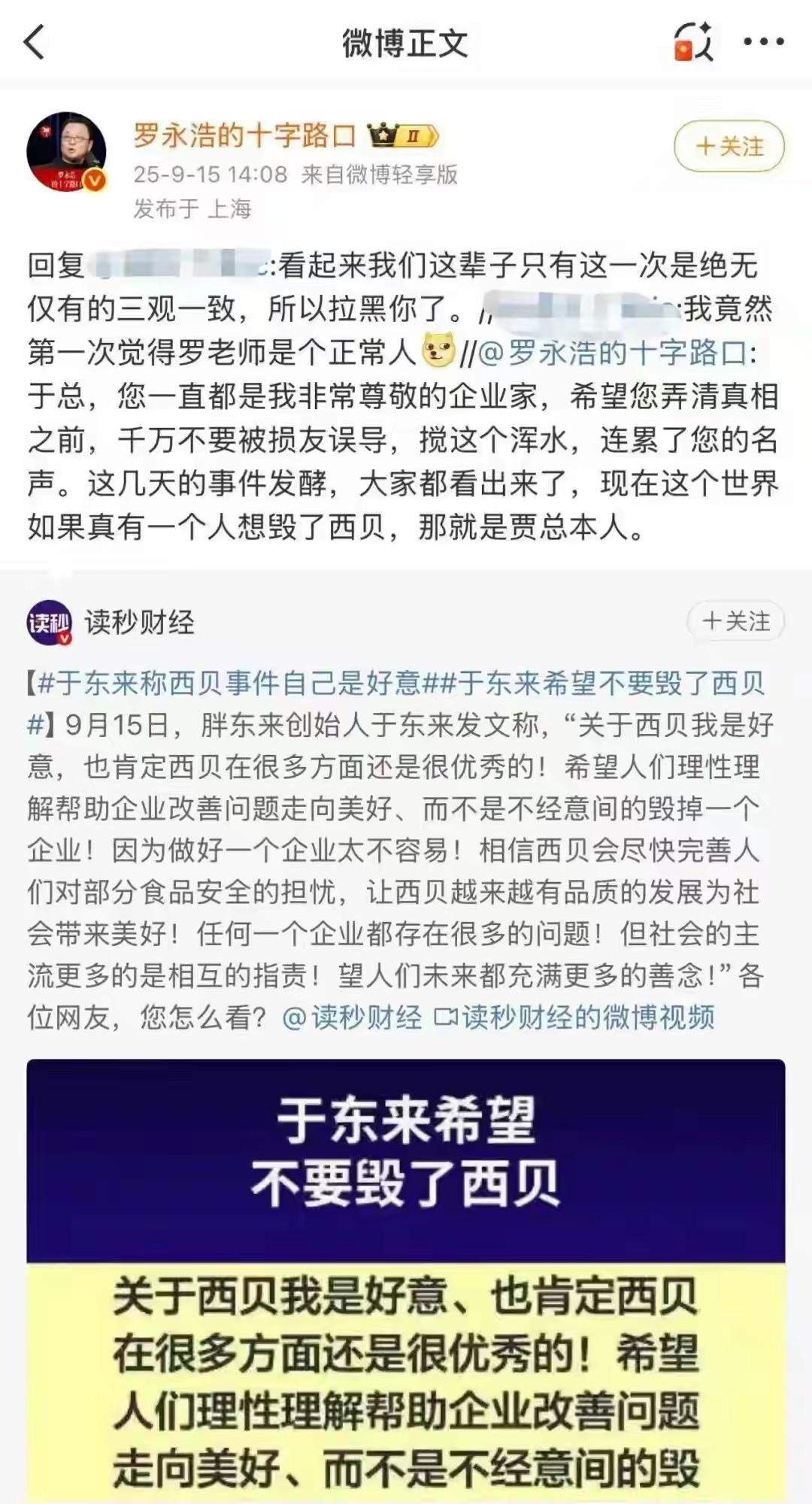【郑永年谈中国为何必须超越西方打造更优秀的人工智能—1】
(南华早报,后篇:)
——多年来,您一直呼吁重建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最近,您也表达了对人工智能时代“知识殖民主义”的担忧。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这些担忧主要是指源自西方的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挑战。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 中所言,宗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而社会和技术的意义则取决于人文和社会科学。
中国研究者学习和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是基于西方的方法,总结西方的实践和经验,然后用它们来解释西方社会。
这些理论无法解释儒家文明、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社会。我们应该充分拥抱我们的世俗文明,从而在国际秩序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速度加快,但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逻辑始终没有改变:信息的输入和信息的提炼。
中国的DeepSeek是成功的,但它产生知识的方式与OpenAI的ChatGPT等模型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生产不再是发散过程,而是趋同过程,这加大了我们依赖西方知识体系的风险。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和战略界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需要格外谨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理念和知识体系,如此浩大的工程,该从何入手?如何学习西方,同时又不至于完全依赖西方的框架?
许多人在使用 ChatGPT 之类的工具时,却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这非常危险。问题在于模型的“喂食”。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近代以来,所有最优秀的论文都是以外语发表的,尤其是英语。即使是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最好的论文也是用英文发表的,因为中国学者认可的顶级期刊主要来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现在,如果你想使用 ChatGPT、DeepSeek 或类似的工具来构建知识体系,很难避免被殖民化的过程。我们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识的供给方式。
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历史记载。但要将这些经验和记载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何况还有40年的改革开放。这些跨越几代人的努力应该用来准备这份食物。
否则,它仍然是单向的,只有西方的输入,没有来自中国的输入。如果我们建立同样强大的中国输入,情况会更加平衡。
我并非排斥西方。问题在于社会科学缺乏真正的中国“故事”。即使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其理论框架仍然是西方的。中国仅仅提供证据——而且佐证往往是不正确的,因为命题本身就存在缺陷。
更危险的是许多中国学者的短视。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声称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知识体系”。但他们只是自说自话。
一些经济学书籍干脆把书名中的“西方”换成“中国”,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
我们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项工作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办成的。
——您提到构建独立的中国知识体系要从实践出发,您认为中国自身的哪些实践值得特别关注?
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例子,它根植于实践。
当时,欧洲革命理论强调城市斗争。一些失败的经验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正统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创新。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开启了农村革命。
邓小平也有创新,例如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猫理论”等。
我们今天有很多创新实践,但并没有发展成为概念理论,而是经常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实践,但这并不奏效。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东西。
社会上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做法,比如深圳发展背后自下而上的故事。
“公民社会”是一个西方概念,隐含着对国家的反对,但中国社会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从国家到社会,没有明确的界限——它是一个连续体。我们的市场和国家也没有严格区分。我们没有西方那种绝对私有制或绝对公有制的概念。
中国古人在两千年前就尝试了井田制,这说明古人追求的是公私结合,这是用西方的框架无法理解的。
——您还提到打破西方的学术垄断至关重要。在当今中美紧张的环境下,一些人可能将此视为中国争夺全球领导地位和话语权的举动。您对此有何看法?
那是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问题。但意识形态不是学者能够掌控的,我们对此只能感到无能为力。
我一直主张,我们根本不排斥西方。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方法论,这很重要。但这些工具所衍生的概念和理论往往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
中国应该借鉴他们的方法,抛开他们的理论建构,重新审视中国自身的实践,发展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就像每个西方国家都有自己鲜明的社会科学特点一样。
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建立一门中国社会科学,这将对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但这并不是一种对抗行为。
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歪曲事实,但我认为,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人是少数。
主流社会看到了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现实,却无法用西方的框架来解释。他们在等待答案。如果我们不给出答案,谁来给出呢?
这并不是要我们封闭自己,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一堆自说自话是行不通的——没有人会理解或接受。
构建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沟通。我们接受西方理论,并非因为强加于人,而是因为其逻辑令人信服。中国应该创造一些同样有效的理论。
——您期待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知识体系的重建在“十五”规划中如何体现?
我认为建立中文知识体系的努力将会加速,因为紧迫性已经存在。
我们常说西方不理解我们、误解我们,甚至妖魔化我们。现在,我们有责任向西方解读我们自己。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我们不能让别人等着我们自己去解读。
我们也应该更加开放。西方的知识体系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我们也必须这样做。真正的知识体系必须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与此同时,我们常常假装了解西方,但实际上只掌握了表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培养一大批精通各种文明的人才。
我认为现在的形势比民国时期更严峻。
费小东为什么能写出《中国农民生活》?他用西方的方法论对中国现象进行了精彩的解读,这可以说是中国独立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现在中西学是分开的,民国时期是融合的。
当前的学术培训主要侧重于可量化和可衡量的东西——ChatGPT 可以做的事情——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真正有价值的方面是那些无法衡量的。
但中国也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丰富的实践经验。
—— 您提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避免过度关注“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如何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您呼吁知识界“去巫术化”(de-witching),即您用来形容猎巫心态的术语?
如今,许多人文学者更像是世俗的牧师,为了追求名气,不断炮制“心灵鸡汤”之类的内容,这种做法在中国盛行一时。这对社会没什么用,确实不好。
如果西方用意识形态的眼光妖魔化中国,中国学者也用意识形态来妖魔化西方,那不是知识体系的构建,而是针锋相对的谩骂。
这毫无价值,是伪学术,或许引人入胜,却不会留下任何持久的痕迹。我们需要自我认知。我们必须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中国智库如何发展才能有效回应国际舆论,提升影响力?您之前对美国兰德公司给予了积极评价。中国的智库机构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美国是西方智库最发达的国家,从服务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兰德公司做得最好。
中国的智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辩护”型,即政府要求其审查的任何事情都予以批准;另一类是纯粹的批评型,即认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这两种类型都不可避免地各有其用武之地。
每个政府都需要有人来评估一项政策是否科学合理。但如果它永远无法断言其不合理,那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智库。同样,如果智库只是简单地宣称政府的每项行动都无用,那它也不能算作智库。
真正的智库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所有领导人也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例如,如果香港智库服务于特首本人,那就可能有问题。如果它服务于香港的利益,那就很好。
——这不禁让人想到软实力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既独立自主又能普遍适用的知识体系?
我认为建设软实力需要四个条件。
首先,你写的东西必须有人读。如果没有人愿意读,它就行不通。其次,它必须能被人理解。第三,理解之后,人们就会接受它。第四,人们不仅接受它,还会传播给其他人。
目前,我们在所有四个阶段都遇到了问题。然而,西方在其中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功。
我们的老师一直在传播西方知识,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写出能进入西方课堂的书籍呢?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在理工科领域或许可以,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呢?
以中国40年内实现8亿人脱贫为例,这在西方也被誉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我们该如何讲述扶贫故事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使用学术语言。如果我们只强调意识形态的正确性,那肯定不能展现全貌。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语言讲述故事,也会阻碍别人向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