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4年,38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命若游丝,临死时,这个差劲的皇帝竟留下了两道“英明”遗诏:第一,废除自朱元璋以来的后妃殉葬制度;第二,释放自永乐以来就被囚禁的“建庶人”,也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儿子朱文圭。
提起土木堡之变,提起朱祁镇,估计人人都骂朱祁镇是“大名战神”,是葬送二十万大军的糊涂蛋;而夸于谦是力挽狂澜的“英雄好汉”。 这个看法,没错,但也不是完全正确。因为历史真相很复杂,即便是后人开了上帝视角,依然难以拨开层层迷雾。 朱祁镇(明英宗)亲政前(1441年),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主政的“仁宣盛世”,表面光鲜,实际上隐患巨大。 为了“省事”,他们放弃了越南(交趾布政使司),让大明南方防线不稳。更严峻的问题是钱粮:边军的“口粮田”(军屯)收入,暴跌到不足洪武时期的5%。 不仅如此,此时大明朝的田赋总额也缩水了近十分之一。这些钱粮真是免了百姓的负担?恐怕不是!大量的军屯田被各级权贵侵占了!朱祁镇继位后,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被严重掏空的局面。 年轻皇帝朱祁镇亲政后,想干点实事,也想当一个好皇帝。朱祁镇最扎眼的一个动作,就是打击一种叫“保举”的选官制度。这制度源于建文时期,被成祖朱棣视为导致冗官、效率低下的“老鼠屎”,废掉了。 但朱祁镇刚上台,这制度就又死灰复燃(并非朱祁镇搞的保举,而是明朝的文臣集团搞的)。朱祁镇在正统六年(1442年)开始狠刹这股风。他为什么干这个?因为保举上来的官员,往往拉帮结派,削弱了皇帝的权威和用人权。他这拳,直接打在依赖此道扩展势力的文官集团脸上。 王振作为掌权太监,名声极差。但换个角度看,他的崛起和权力,根源在于皇帝需要他来对抗庞大的文官。他是皇权的延伸,干了很多皇帝不方便亲手干的事,比如压制那些不听话的官员。说他“忠”,也许是忠于皇帝本人,而不是抽象的大明。 土木堡这场大败,疑点重重,朱祁镇一个人犯蠢,真能把局面搞这么糟?土木堡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史料记载是因为缺水!这就怪了!土木堡边上就有河!七月八月正是雨季,按理说不该缺水渴死大军。谁在控制水源? 英宗亲征路线并非绝密。常年在宣府大同当总兵的杨洪等将领,难道不知道皇帝动向?边镇的情报系统(烽火台)为何失灵?瓦剌也先数万人马怎么能悄无声息地突破长城防线? 皇帝被困土木堡,近在咫尺的宣府总兵杨洪为何按兵不动?事后他直接带主力撤回了北京(不久就死了),他的人马去哪了? 于谦在朱祁镇出事前一年才从地方(山西、河南巡抚)调回京城,任兵部侍郎。朱祁镇就在他刚刚离任的管理区域核心地带出大事,作为精通边务的老臣,他对后方潜在危机有没有察觉? 正统六年(又是正统六年!),于谦主张把军队管理的粮仓移交文官。这个举动意味着,军队的命根子——粮食,被文官系统牢牢掐住了。这是帮军队,还是加强文官控制? 土木堡之后,于谦成了兵部尚书,手握重兵大权,堪称“没有宰相名头的宰相”。 他干了几件大事:恢复被朱祁镇打压的保举制度! 这个朱棣和朱祁镇都极力清除的“冗官制造机”,于谦又让它复活了;停掉了福建银矿开发(影响朝廷收入);没有深究通州粮仓神秘未被焚毁事件(粮仓关乎京师命脉);取消了区分南北的科举地域录取制度。 谁是“忠臣”?谁在“为大明朝”?于谦确实在京城保卫战中功劳巨大。但看他主持朝廷后恢复保举制度这一条,就很值得深思。 朱棣、朱祁镇父子俩都把这个制度视作败坏大明的祸根,朱祁镇一上台就打压它,朱祁镇“北狩”(被俘)后它就立刻复辟,等朱祁镇夺门复辟后,它又被立即铲除…… 于谦作为政策的强力推行者,他究竟是没意识到其危害,还是这政策本就有助于巩固他和他代表的文官的权力? 朱祁镇想打击权贵侵占军屯、打击可能导致冗官的保举,试图加强皇权控制。结果,他在自己家门口的核心防区遭遇了史上少有的惨败。 手握重兵的边将、掌控军队粮草的文官、以及战后迅速填补权力真空并重建被皇帝打压的旧制度的于谦一派……这真的仅仅是皇帝昏聩和宦官能解释的吗? 历史的答案,往往藏在权力的夹缝里。 朱祁镇的“英”或许不是雄才大略,而在于他曾试图夺回被侵蚀的皇权,却一头撞进一张无形的大网。 于谦的“忠”不容抹杀,但他在关键时刻推动的选择,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朝廷的格局和未来冗官冗费的积重难返。 土木堡之变,绝不只是皇帝带错路那么简单,它是一场大明帝国权力格局剧烈震荡下的风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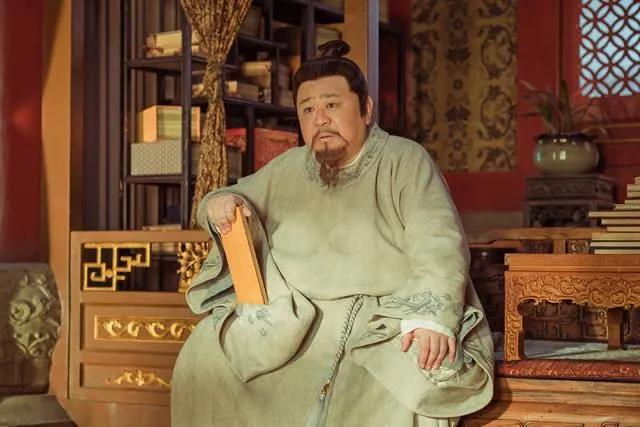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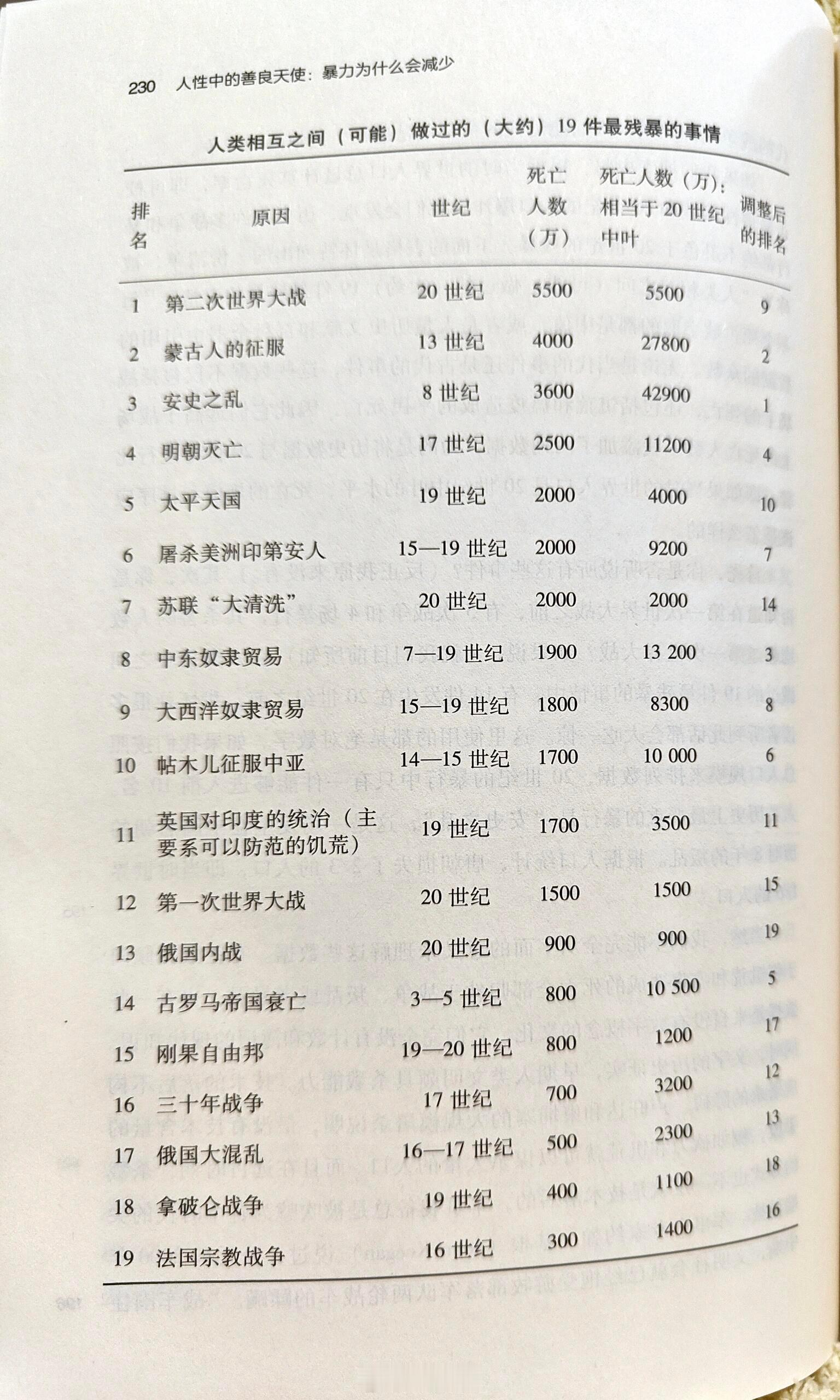



fish
洗白了魏忠贤,开始洗白留学生和王振了;抹黑了袁崇焕,开始抹黑于谦了。历史虚无主义流行,牛🐮🐮!
追梦人 回复 08-31 16:16
网络上标新立异,才能更好的恰流量
明月空空 回复 09-05 17:44
袁都督本身就一身黑
张衡
阴谋论加事后诸葛亮。朱祁镇被放回来后的事更是令人发指。
心想事成
于谦和袁崇焕死的一点也不冤
老大虎 回复 09-23 17:57
所以,汉将投降满清就对了
老大虎 回复 09-23 18:01
给大明续命二百年的忠臣不被皇帝容,不被尔等平头百姓容,所以满清统治中国就对了
千泉
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复杂的,视角独特,内容详实,给小编点赞👍
garson
朱棣、朱祁镇父子俩都把这个制度视作败坏大明的祸根~~他俩是父子吗?金~水~木~火~土~金…,朱元璋~朱允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钰)~朱见深~朱佑樘~朱厚照(朱厚熜)~朱载坖~朱䦀均~朱常洛~朱由校(朱由检)
雨过天晴 回复 10-14 14:23
我也刚想说这一点!伦理关系都搞不清楚的人居然大言不惭的解读历史!这年头真的是人是鬼都敢跑出来卖弄!关键还胸无点墨!
garfield
很新颖 但真假难辨
境·界
个人认为抽象的国家还是很重要的
用户17xxx69
连大明战神都要洗了
一只叫豆豆的猫
小编学过历史吗?
用户15xxx89
朱祁镇是朱棣的重孙子,还尼玛父子
明天会更好
要是朱标一脉就好了 朱棣后代很多庸才
用户13xxx45 回复 10-08 05:50
朱允文连庸才都算不上,根本就是蠢材,还在这里意淫
1a 回复 09-02 13:11
如果都是朱允炆那样的当皇帝,朱标的后代也不怎么样。可惜的朱雄英早死,朱允熥被吕氏养废。好好的嫡子被庶子替代上位
ABCDE12345
现在挺于谦的那些人除了知道个北京保卫战,都不知道于谦到底干过什么。
监督员 回复 09-21 20:15
你知道于谦干了啥?要有一定的证据,而不是瞎编的
ABCDE12345 回复 监督员 09-22 09:29
额外说一句,对于你们这种张嘴就是“要证据”的人,我已经疲劳了。不知道你如何,反正我遇到的“要证据”的人,你们或者说你们大部分人要的是把“于谦是奸臣/权臣”这样的字句明确写出来才叫证据,否则都是假的。你们的证据逻辑可以形容:因为圣旨是汉献帝颁发的,所以汉献帝不是傀儡;海昏侯刘贺是群臣奏请太后废除的,所以不是霍光废的,霍光不是权臣。
今生跟随Jesus
编正统道藏也是他的一大功绩。
用户10xxx87
小编真能意淫
晓燕
我们现在不知道明朝的任何历史!满清文字狱堪称造假一绝,杀光知情者,烧光史书,再推行汉奸举报可疑知情者,株连全族,最后它们想怎么编造明史都行?它们不会将老朱家任何一句好话!连朱元璋的画像都造假的,只此一家。别的王朝,正史不对,还有野史,但满清持续295年的文字狱,不允许有任何野史。这种文字狱贯穿了满清始末,所以明史极度不真实,甚至可以说一个字都不要信!讨论一段错误虚假历史,你们可真有意思。
天天向上
别的不说,辈分不能乱吧!
一点山间火
说来说去,就是朱标死早了,才有了后续系列的事
苍天
朱棣这一脉是不是有什么遗传病,一个比一个短命,朱高炽48,朱瞻基36,朱祁镇38,朱祁钰29,朱见深41,朱佑樘35,朱厚照30
8431188 回复 10-15 15:04
有能力的都活不久
龍曦う羽 回复 10-15 22:10
因为权利不平衡,以前是藩王勋贵文官三条腿,藩王被禁锢后就只剩勋贵和文官,后面直接是文官一家独大。都要天子垂拱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