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73年,福州军区副司令的妹妹进城,特意来看望他,谁料,妹妹对他说:“哥,我儿子在你手下当兵,还请你多加照顾!” 在中国那些闪耀的将军名单里,朱绍清是个挺特别的人,他是个开国少将,当过福州军区代司令员,也做过福建省委副书记,权力挺大,但因为他“铁面无私”而出名,甚至有人觉得他“不近人情”。 不过,朱绍清的人生其实就是在原则和亲情间不断划界限的探索,尤其是在面对亲人时,他的选择和坚守,让人特别感动。 朱绍清的坚持,是在苦水里泡出来的,他家在湖南华容县的栗树屋场,特别穷,十四岁那年,他就加入了红军,在枪林弹雨中滚了一辈子。 光是在长征路上,朱绍清就受了六次伤,命都是捡回来的。这种从血与火中磨砺出的信念,成了他一生的底色。 革命这条路,也让他的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哥哥嫂嫂被国民党反动派杀了,家里只留下妹妹一个人,带着瘫痪的母亲艰难生活,这份对家人的亏欠,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 朱绍清有一套自己的“三帮”原则,界限划得很清楚,帮集体农业发展,可以;帮符合政审体检条件的普通人家孩子参军,可以;帮得了疑难杂症的群众找医找药,他甚至自己掏钱。 1970年,老家急需拖拉机搞生产,村干部托他妹妹找上门,这是公事,他二话不说,立马通过武汉军区的关系给办妥了,还特地选了离家乡近的地方,方便运输。 可事办完,他脸一板,严肃地告诉妹妹:“以后谁找你帮忙安排工作,就是你自己的孩子,我也不答应!” 两年后,外甥曾克平到了当兵的年纪,他自己很争气,政审、体检都合格,朱绍清这才帮他入了伍,正好分在福州军区,妹妹心想,这下儿子在舅舅手下,总能得点照顾吧? 没想到,朱绍清直接给外甥立下“约法三章”:一年顶多来看我一次,机关大门不准进,必须在基层好好干,更不许提我的名字办任何事! 曾克平把舅舅的话记在心里,在部队八年,他愣是没跟任何人提过自己的背景,靠着一身汗水,在军事大比武里拿了好多奖,成了训练标兵。 直到1976年,朱绍清亲自观摩比武,看到外甥在场上生龙活虎,才在众人面前自豪地“官宣”:“那个兵,是我外甥。”他要的是外甥自己挣来的荣誉。 1973年,妹妹来部队看儿子,听说哥哥就在几百米外的村里检查工作,满心欢喜地等着。 可从早等到晚,也没见着人影,妹妹委屈极了,直接跑到福州,对着朱绍清就哭了,把当年自己怎么一个人照顾母亲的苦全倒了出来,求他看在这份情上,多关照一下外甥。 然而,朱绍清听着心里五味杂陈,可嘴上还是那套硬道理:领导搞特殊,部队的风气就坏了,当兵的就得靠真本事吃饭,妹妹听不懂这些大道理,这个心结,她揣了很多年。 朱绍清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他一辈子信奉“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建国后因公回乡,在招待所里,他硬是不让妹妹跟自己同桌吃饭,他夫人黄晓虹只能在一旁解释,这是公家的饭,不能添人。 1987年,他都退二线了,在湖北整理军史,妹妹去看他,饭点到了,还是被“请”走了。 六十年代回乡,地方派了辆高厢军车来接,他拒绝了别人递来的板凳,自己一使劲就翻了上去,地方上好心在他家门口设了个岗哨,也被他遣散了,说这是搞形式,他宁可在自家堂屋用门板搭个床睡,也绝不住招待所。 可是有一次在莆田视察,朱绍清听说一个贫病交加的老大娘,嘴里念叨着:“只要还有一个群众受苦,就是我的失职。”他立刻安排部队送去大米,派军医全力救治,临走时,把自己和随行人员的钱都掏空了塞给大娘, 1989年,朱绍清将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用尽最后的力气,在纸上颤抖着写下一个“党”字。 夫人黄晓虹懂了,在他耳边轻声承诺:“你放心,党费,我一定替你交齐。”听到这句话,他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主要信源:《人民网——我军反腐败斗争的历史镜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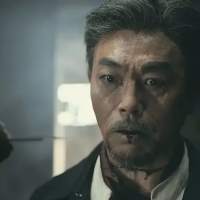
用户15xxx57
高风亮节
武哥
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革命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