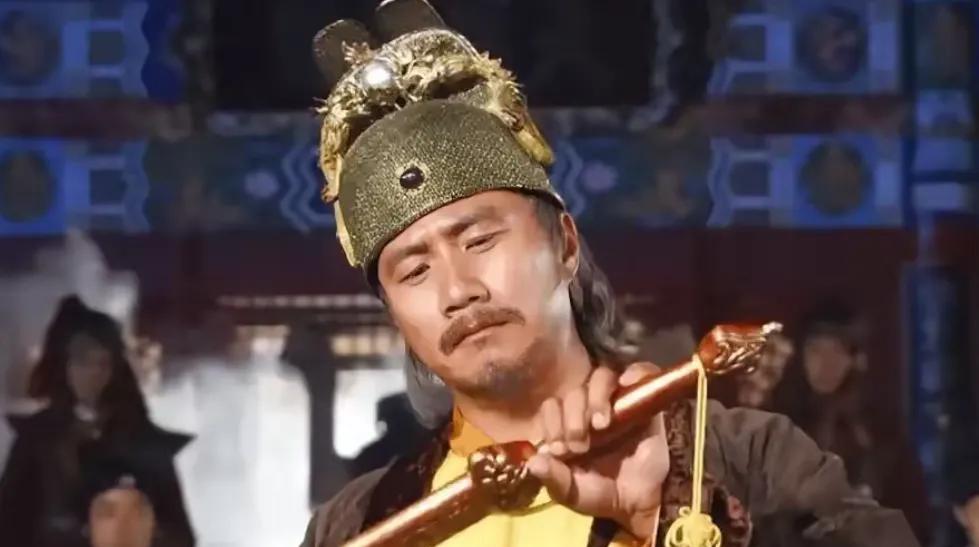1403年,明朝开国功臣郭英临终前,把儿女叫到身边,语重心长道:“朱元璋杀了那么多有功之臣,独留我和耿炳文,朱棣上位后,耿炳文被逼死了,唯独我安然无恙,可知为何?”儿女纷纷摇头,等待着父亲的教诲。 郭英靠着床头,喘得厉害,他的眼神还亮,盯着跪在眼前的几个儿女,一字一句地说着这话。屋里一下子静了,连风都像被这话拦住了脚步。 “朱元璋杀了那么多老兄弟,李善长、蓝玉……一个个都没留下,耿炳文也走了,可我,郭英,还坐在这儿,说话给你们听,你们就不琢磨琢磨是为什么?” 1403年,永乐元年夏天,南京城正是热得出汗的季节。朱棣刚刚登上皇位,朝堂上刀光剑影还没散。 郭英,这位在洪武年间打下大明江山的老将,此刻却不是在回忆战场,而是在交代活命的本事。他没说打仗的事,只讲怎么“活着”。 “你们知道蓝玉案吧?”他瞥了一眼几个儿子,目光像刀子,“那一年,我就在宫外候着。消息一出来,整座南京城都在抖。 蓝玉死得惨,连带着几千人跟着倒霉,那天我回府,第一件事,是把手里的兵权交了,亲军的令牌,我亲手捧着,送回宫里去了。” 他说这话时很平静,好像在说一顿饭吃了什么菜,但他身边的一个儿子却忍不住插嘴:“爹,那您不是让人看轻了?” 郭英咳了一声,冷笑:“看轻?你以为朱元璋是瞎子?我把兵权交出去,他才放心我没二心。你们要记住,在皇帝眼里,最危险的,不是犯错的人,而是‘太对的人’。 什么都对,功劳太大,那你离死就不远了。”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角落里的女儿身上:“你嫁给朱植,是咱们郭家的荣耀。但是从你进王府那天起,我就不敢多出门,也不敢派人上门问事。你是皇亲,我不是皇帝的亲戚,我只是个功臣,功臣跟皇亲,永远是两回事。” 屋里有点闷,窗外的蝉声喧天,像是催命的鼓点。 “我说耿炳文,你们都记得吧?”郭英忽然提起这个老兄弟,语气慢了下来。 “那是个好人,靖难的时候,他替建文守城,尽心尽力。可朱棣上位后,他还能活吗?他是前朝的忠臣,新皇的眼中钉。最后是自己找根绳子吊死的,不是他想死,是他知道,不死更惨。” 他说到这儿,眼里有点湿了,没人敢说话,几个儿女低着头,只听那把老嗓子继续说。 “朱棣上位第三天,就有人参我一本,说我侵占田产。我知道,这是试探。他想看看我是硬骨头,还是识时务。我怎么办?我跪下了,认了,说我贪财,说我该罚,你们猜朱棣怎么着?” 他盯着儿子们,嘴角翘起一点:“他笑了,他说:‘郭英老了,贪点田地不打紧。’罚是没罚,还赏了我一匹锦缎。” “你们看明白了吗?他要的,不是清官,而是听话的人,你越无害,他越放心,你越像英雄,他越怕你。” 说到这儿,他喘得更厉害了,像是把压在胸口几十年的石头都掀了。 “你们以后要记住,咱郭家活到今天,不是靠打仗赢的,是靠‘知止’,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认,什么时候该装傻。” 门外传来风声,像是有人路过,又像是命运擦肩而过。 “后来你们大哥做了件事,我是满意的。”郭英侧过头,含糊地说,“朱棣那会儿查建文旧臣,满城风雨。 你大哥把咱家库房打开,捐了一大半家产犒军,你们知道结果吗?朱棣亲手给咱家写了‘忠孝传家’四个字,你说值不值?” 儿女们点头,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郭英咳了几声,闭了闭眼。 “你们别以为我就没想过,当年鄱阳湖边,我给朱元璋挡箭那一刻,他说要跟兄弟们共享天下。可后来呢?他共享了太平,皇位只给了他儿孙,我们这些人,只能在边上看。” 他说这话时,声音轻得像风,像是说给自己听,又像是说给后人听。 “我不是没遗憾,但我活下来了,咱郭家也活下来了。这就够了。” 他睁开眼,最后看了儿女一眼:“记住,知止,才是长久。” 第二天清晨,郭英去世,没有哭声,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哀悼,他的棺椁悄悄送出府门,像他这辈子一样,不张扬,不显眼。 可谁都知道,从洪武到永乐,死了一批又一批开国功臣,最后站着走完这条路的,叫郭英。 他不靠运气,不靠权谋,只靠一个“知止”的智慧,把郭家带进了下一个百年。 信息来源: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