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了,不需要那么多钱,”2020年,一生抠门的大学教授王泽霖,却大手一挥捐出了8208万元,女儿知道后只说了一句话。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2020年,一个消息在校园里炸开了锅,82岁的王泽霖,把自己账户里全部的8208万元捐了出去。 这位被学生称作“抠门教授”的老人说了一句话:我老了,不需要那么多钱,女儿知道后,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爸,您给我的,比钱更珍贵。 王泽霖抠门是出了名的,上课时,他经常穿着打着补丁的外套,袖口磨破了也照常穿,吃饭更简单,三两咸菜加一碗米粥就是常见的一顿。 他常年住在老教师宿舍里,不肯换新家具,出行靠一辆电动车或者吱呀作响的自行车,别人眼里的清苦,他自己却习以为常。 可就是这个对自己斤斤计较的人,买实验设备时却毫不手软,别人还在犹豫,他早已把三十多万的超速离心机买下,有人调侃他舍不得买新衣,却大手笔砸钱买机器,他总说,钱要花在刀刃上。 王泽霖的初心来自农家炕头,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兽医,蹲在养殖户的鸡舍和猪圈里,常常一坐就是半天,看着农民因为一场疫情愁得睡不着,他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用科技改变这种局面。 为了这个目标,他从山西到南京,从基层行医到硕士深造,再到河南农大建实验室,走了一条常人难以想象的路。 他花几年时间收集病例,手写的诊疗笔记摞满半个书柜,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最后转化成了专利和新兽药,成为农民手里最可靠的屏障。 科研的路从来不平坦,1984年到河南农大任教时,他面对的是空空如也的实验环境,没有钱买设备,他白天教书,课余时间骑车去养殖场诊疗,靠一次次出诊攒下积蓄。 十年间,他攒下了400万,这是那个年代万元户都稀罕的财富,他没有把这笔钱留给家人,而是全部捐出来,建了两栋实验楼。 那一天,校园里的人都看见一个穿着旧衣的教授,拿出全部家当换来先进仪器。 自那以后,科研条件逐渐改善,他的成果一项接一项地突破,最终获得了12个新兽药证书,彻底改变了我国在家禽疫苗上的被动局面。 这种花钱方式,成了他一生的选择,1994年实验楼落成,他没有参加剪彩,而是留在办公室整理资料,2005年,一家药厂慕名而来,本想用五万买专利,最后以五百万成交。 他拿到钱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出175万给学校和院系,又凑齐一百万捐给学会。 2014年,四家药企愿意出近两千万做研发,只换一个优先使用权,这在外人眼里像是吃亏,但业内人都明白,王泽霖团队的成果转化率是百分之百,合作是一种信任。 到了2019年,账面上的数字让人吃惊,专利转化收入累计达8208万,他和妻子住的依旧是旧公寓,出行还是靠电动车,每月一万五的退休金,他们都花不完。 存折上的数字越滚越大,他反而越来越清醒,他发现学校的P2实验室无法研究高危病原,升级P3实验室需要巨额投入,他想来想去,决定把这些钱全部捐出。 钱捐出去之后,他并没有向外界解释太多,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生活所需不过几件旧衣、几顿清淡饭菜,剩下的都是负担。 对他来说,钱真正的价值,是能让更多学生在先进实验室里做研究,能让科研成果更快惠及农民。 等到2023年P3实验室剪彩那天,师生都希望用他的名字命名,他摆摆手,说未来能攻克禽流感的年轻人,才是最好的金字招牌。 他的女儿对父亲的选择从未抱怨,小时候,她见过父亲把破了口子的皮鞋粘了又粘,也见过家里简陋的饭桌和旧家具。 她本以为这是家境拮据的无奈,直到多年后才明白,父亲是有意为之,他省下的每一分钱,最终都流向了科研和学生,等到她看到账户里的余额时,才彻底理解父亲这几十年的坚守。 一个一生抠门的老人,把节省变成习惯,把慷慨留给国家和人民,他用八千多万建实验室,却依旧住在旧公寓里;他穿着旧衣,却让学生穿上实验服走进世界前沿。 那一句“我老了,不需要那么多钱”,背后是大半生的付出和信念,女儿的那句回应,正好点明了最珍贵的遗产:不是财富,而是精神。 在很多人眼里,王泽霖这一生都像个谜,为什么他对自己这么吝啬,对科研却毫不吝惜,可在那些养殖户眼里,他的选择最实在,因为“禽病防疫找王泽霖”早已成为口口相传的信任。 对于学生来说,他留给他们的不是金钱,而是榜样,一个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了一道屏障,让无数养殖户心里有了底气,让国家的农业多了一层保障。 八千多万捐款的票据如今陈列在校史馆,数字精确到个位数,旁边放着泛黄的病例笔记,每一页都写满了他在养殖户炕头上的心血。 相比这些厚厚的纸页,存折上的数字更像是附属,真正的财富,已经传递给了更多人。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光明网——“抠门”教授王泽霖,8000多万全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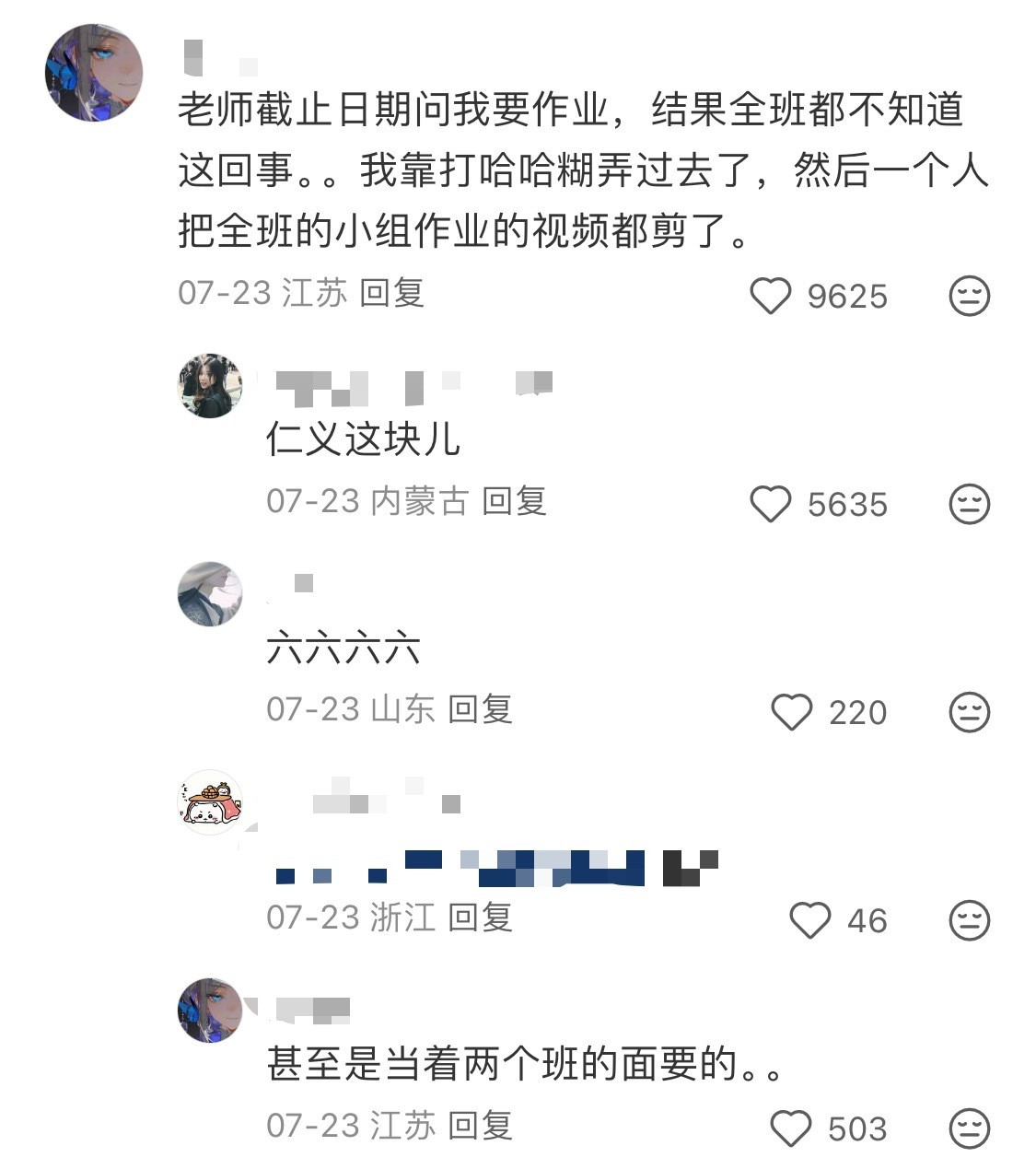





用户10xxx78
八千多万,工资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