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强硬,毛主席得罪了三大阵营—— 一是因为强硬,得罪了欧美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这一强大阵营!这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毛主席下令驱逐了北京东郊民巷的旧政权时代的,欧美各国驻华大使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但就在那天之后不久,一场看似“外交礼仪”的风波,实则成为新中国彻底与旧世界秩序决裂的标志性动作。 北京东交民巷,这条长不过一公里的小街,在清末民初的半个世纪里,曾是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国中之国”。 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在此设立使馆、兵营、法庭、邮局,甚至拥有路权与治外法权。中国人在这里不仅无权行使司法,甚至骑马都需下鞍避让。 而毛泽东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外交大事,就是在1949年末下令:所有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其驻华机构必须撤离东交民巷。 这是一次象征意义远大于技术意义的举动。 它不仅终结了旧中国“领土主权分裂”的屈辱岁月,更宣告了一个全新的外交原则正在确立:从此以后,谁尊重中国主权,谁才能在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存在。 说白了,这是一次彻底的“主权清零”。而这场清零,得罪的,不只是几位外交官,而是整个西方秩序的核心。 1950年,《纽约时报》在一篇评论中直言不讳:“新政权拒绝承认任何战前协议,这是对全球契约体系的公然挑衅。” 但问题在于,他们口中的“契约”,正是几十年间用军舰、炮火和赔款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条约”。 毛泽东没有退让。他甚至在1950年公开表示:“中国人不欠你们一分钱,欠的,是你们几百年来从我们这里夺走的。” 而这仅仅是毛泽东“得罪的第一个阵营”。紧接着到了1950年,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 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列强发起的第一次硬碰硬的军事博弈。面对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的挑衅,毛泽东没有选择妥协,而是果断决策:“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付出了19万余名烈士的代价,击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迫使对方在1953年坐回谈判桌前签署停战协定。 而正是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强硬路线,让西方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不是可以驯服的新兴国家,而是必须重新评估的战略对手。 但毛泽东得罪的远不止西方。第二个被他得罪的,是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地主阶级与官僚资本。 1947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写下《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明确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路线。 与党内王明等人主张“富农不动”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强调:“革命的根本,就是土地问题。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就没有人民政权的根基。” 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从1949年到1953年,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3亿多农民的土地重新分配,直接触动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权力结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启动,毛泽东提出“三大改造”方针,完成了对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收归国有。156项苏联援建工业项目落地,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而这一系列“利益再分配”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罪了第三个阵营:党内保守派和“缓变派”。 早在1931年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就遭到所谓“经验主义”的猛烈批判。 1935年长征途中,他与张国焘的对峙几乎导致党内分裂。 而到了1962年,面对党内提出的“三和一少”(即对外和解、对内稳定、少搞运动)路线,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和平是要争的,但斗争不能忘。” 这种不向任何势力妥协的政治风格,既赢得了人民,也注定了其在体制内外频繁处于“孤帜难撑”的状态。正如他自己在1968年所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但我们要理自己。” 说到这里,有必要重新理解“强硬”二字的含义。毛泽东的强硬,并非暴烈,而是斗争哲学的系统表达。 他不是简单地“对抗三大阵营”,而是在用一整套战略体系,主动破局旧秩序,重塑国家主权、经济结构与国际话语权。 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把美苏定为第一世界,把日本、欧洲等当作第二世界,把亚非拉归为第三世界,并明确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一员”。 这一理论,打破了冷战的“二元对立”,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地缘政治的自我认同坐标。 而在实践中,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成为第三世界合作的标志性工程,5.6万人次参与、9.88亿人民币无息援助,换来的不是经济红利,而是国际尊重。 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76个国家投票支持,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亚非拉。这不是外交手腕的胜利,而是“强硬立场”赢得的道义共识。 今天再看毛泽东在东交民巷下的那道命令,不是愤怒的象征,而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不是“得罪”的开始,而是“重塑”的起点。 毛泽东从未怕过得罪谁。他怕的,是中国人永远低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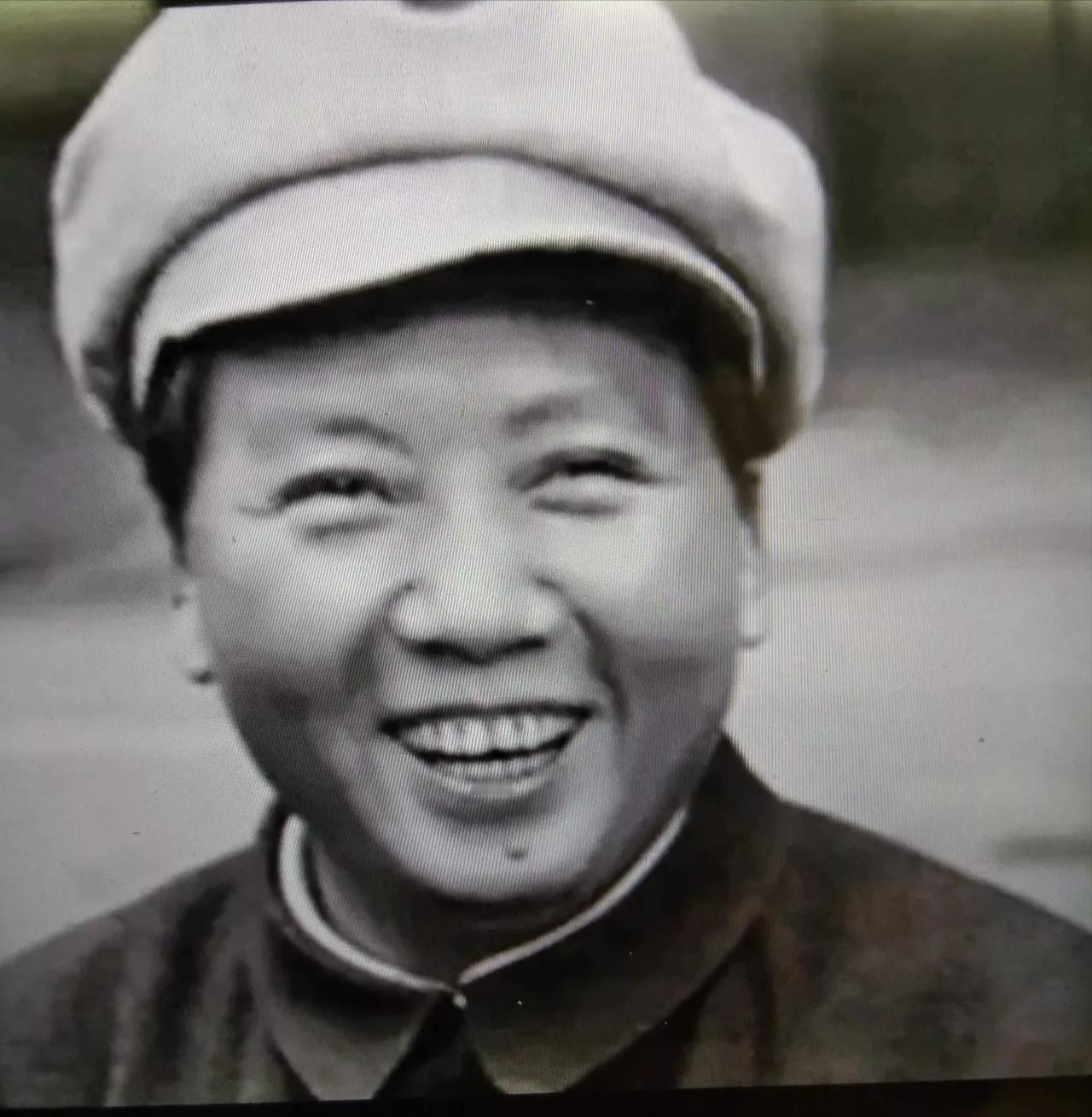









㢲戥
中国不是要遵守规则的,是要给世界立规矩的。那时中国一穷二白,你换蒋介石试试,他敢不敢说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