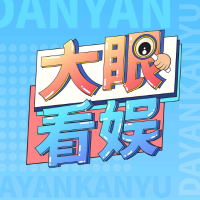1993年,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未经允许下,擅自做了个重大决定,在《新闻联播》播出之后安排了一段30秒的广告。广电部部长知晓后,愤怒道:“怎么回事?杨伟光怎么能这样做!”
此时的杨伟光正站在部长办公室门口,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烟盒。
他知道这场风暴躲不过去。
台里的摄像机已经老得掉漆,上周录制《正大综艺》时,三号机突然黑屏,导演当场急得掉眼泪;
编辑室的磁带机经常卡带,技术员要用螺丝刀敲着才能运转。
国家拨款仅够维持日常开支,想买新设备,无异于痴人说梦。
半个月前,他在地方台考察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某省台在电视剧前插播的广告,让他们半年就攒够了买转播车的钱。
回来的火车上,杨伟光盯着窗外掠过的农田,心里算着一笔账:《新闻联播》后的时段全国收视最高,哪怕只播三十秒,收入也能顶上大半年的设备维修费。
可当他把想法报上去时,得到的回复是 “再研究研究”——层层审批下来,最早也要等到来年春天,而台里的设备已经等不起了。
播出前一晚,杨伟光在办公室待到深夜。
编辑室传来技术员的抱怨:“杨台,这台机器再修不好,下周的《焦点访谈》都录不了。”
他掐灭烟头,突然对值班导演说:“明天《新闻联播》结束后,加一条三十秒广告。”
导演愣住了:“没批下来啊……”
“出了事我担着。” 杨伟光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那条白酒广告播出时,他守在监控室,手心全是汗。
画面从新闻联播的结束曲切到广告,再无缝接回天气预报,流畅得像早就设计好的流程。
第二天一早,观众来信堆成了小山,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是 “没注意到”“三十秒不碍事”,只有少数人问 “是不是电视信号出了问题”。
可这份平静没能持续多久,部长的电话就打到了他的办公室。
“你知道这有多严重吗?” 部长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压抑的怒火,“《新闻联播》是什么地方?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你敢在这儿插广告,谁给你的权力?”
杨伟光没有辩解,只是把一沓设备故障报告递过去:“部长您看,这是上个月的维修记录,光是摄像机就坏了十七次。再不换设备,明年可能连春节晚会都录不全。”
他指着其中一页,“这条广告收入,够买三台新摄像机。”
沉默在办公室蔓延。
部长翻着报告,手指在 “磁带机卡壳导致新闻延时播出” 那行字上停了很久。
“下不为例。” 最终,他丢下这句话,起身时又补充道,“钱必须专款专用,一分都不能乱花。”
杨伟光走出办公楼时,阳光刺眼。
他立刻让人把广告收入打进专用账户,第一个订单就是给新闻中心换四台摄像机。
供应商送来设备那天,技术员们围着新机哭了——这是台里五年来第一次换全新设备。
没过多久,央视开始公开招标广告时段,孔府宴酒以三千多万元拍下全年标王,消息传开,全国商家都疯了似的往央视跑。
那些年,杨伟光踩着晨露去各部门巡查,总能看到新换的编辑机、转播车,听到机房里传来的笑声。
有次他路过广告部,听见工作人员在打电话:“明年的黄金时段?早就被订完了,您得排队。”
而观众们渐渐习惯了《新闻联播》后的广告,甚至有人等着看 “今天又有什么新牌子”。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就不怕被撤职吗?
杨伟光望着央视大楼上的卫星接收器,慢悠悠地说:“怕啊,但设备坏了播不出节目,老百姓骂的是央视,不是我一个人。”
他没说的是,那次冒险之后,广电部很快出台了电视台广告管理办法,而央视的广告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不仅换了全套设备,还建起了新的演播大楼。
1998年春晚,当高清摄像机捕捉到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时,杨伟光坐在观众席里,想起1993 年那个忐忑的夜晚。
那条三十秒的广告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不仅为央视激起了涟漪,更让中国的媒体行业看到了商业化的可能。
许多年后,人们还记得那些年的央视广告,却未必知道,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为了修设备而 “先斩后奏” 的决定。
而那个拍过桌子的部长,后来在会议上说:“有时候,改革就是需要一点敢闯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