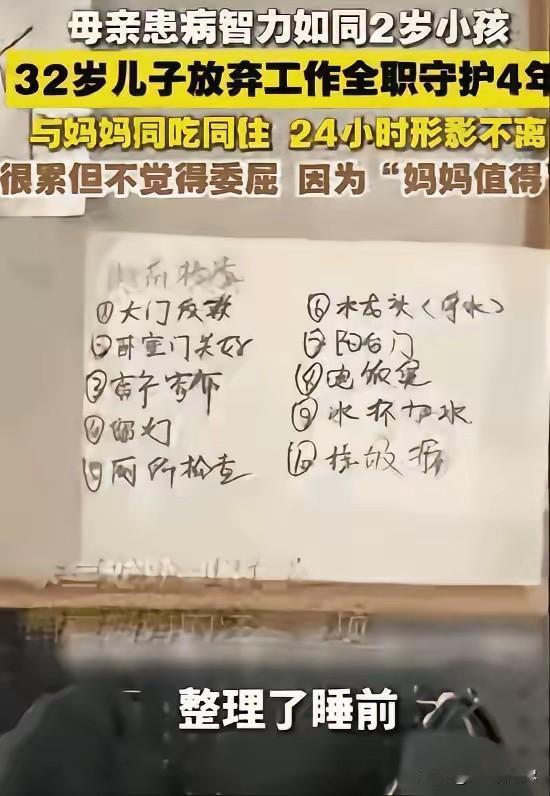我叫多杰,是个藏族汉子。 以前,我满脑子想着探矿,直到见过盗猎分子对藏羚羊做的事——从那以后,我抵押了草场,一头扎进博拉木拉无人区,成了一名巡山队员。 后来的事,你们大概听说了。我被最信任的兄弟出卖,含冤而死,在海拔五千米的冰河里躺了好些年。 但今天我想跟你聊聊,我走后发生的事。 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白菊。 那丫头性子比男娃还刚,我失踪后,她活成了另一个我——带着巡山队成员跟盗猎分子玩命。她跟小邵离了婚,我知道为什么:那丫头看见小邵就想起我,心里跟刀割一样疼。 小邵那小子,刚开始就是个追热点的记者,浮得很。后来跟着白菊进过几次山,见过藏羚羊被剥皮的惨状,见过我那些弟兄们啃干粮睡雪地的样子,慢慢就变了。 他俩复婚那天,我不在,但我看见了。 就在我们以前巡护的那片草原上,格桑花开得正好。小邵说:“以后再也不分开。”白菊那个从不掉泪的丫头,眼眶红得像雪山上的晚霞。 值了。 老韩跟白芍走到一起,倒是没想到。老韩那人轴,认死理,为我的事跑了十年没放弃。他俩能搭伙过日子,挺好——都是被命运亏待过的人,知道怎么疼人。 孟耀辉那畜生,我就不多说了。当初我救了他一命,他背后捅刀子。勾结盗猎的,害死人的,手上沾血的——最后被击毙在无人区边缘,活该。“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这话是我活着时候常说的,现在应验了。 白及和白椿那两个孩子,都走过弯路。一个曾,误入盗猎团伙;一个贪心,差点被利益迷了眼。好在最后都醒了。白椿拿到孟耀辉的罪证,帮我破了案;弟兄合伙开了环保公司,扎措和桑巴也加入了他们。 扎措那小子,执拗起来比我当年还甚,一天看不见藏羚羊就浑身难受。桑巴务实,懂门道,有他俩在,我更安心。 最让我欣慰的,是扎西。 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时候总跟在我屁股后头转,听我讲巡山的故事。后来我走了,他考上了大学,我以为他会留在城里,过安稳日子。 毕业那天,他背起行囊,去了博拉木拉自然保护站。 他说:“多杰父亲没走完的路,我接着走。”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高原人的活法——人死了,魂还在;魂散了,精神还在。一代人倒下去,一代人站起来。 我的名字刻在了守护碑上,沉冤昭雪,追封烈士。但说实话,比起那些虚的,我更高兴看到他们好好地活着,守护着这片我用命爱着的土地。 生命树是什么? 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一代人——是扎西接过我的枪,是白菊带着巡山队继续走,是所有愿意为这片高原豁出命去的普通人。 剧终了,守护还在继续。 愿高原净土永存。 愿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索南多杰 白菊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