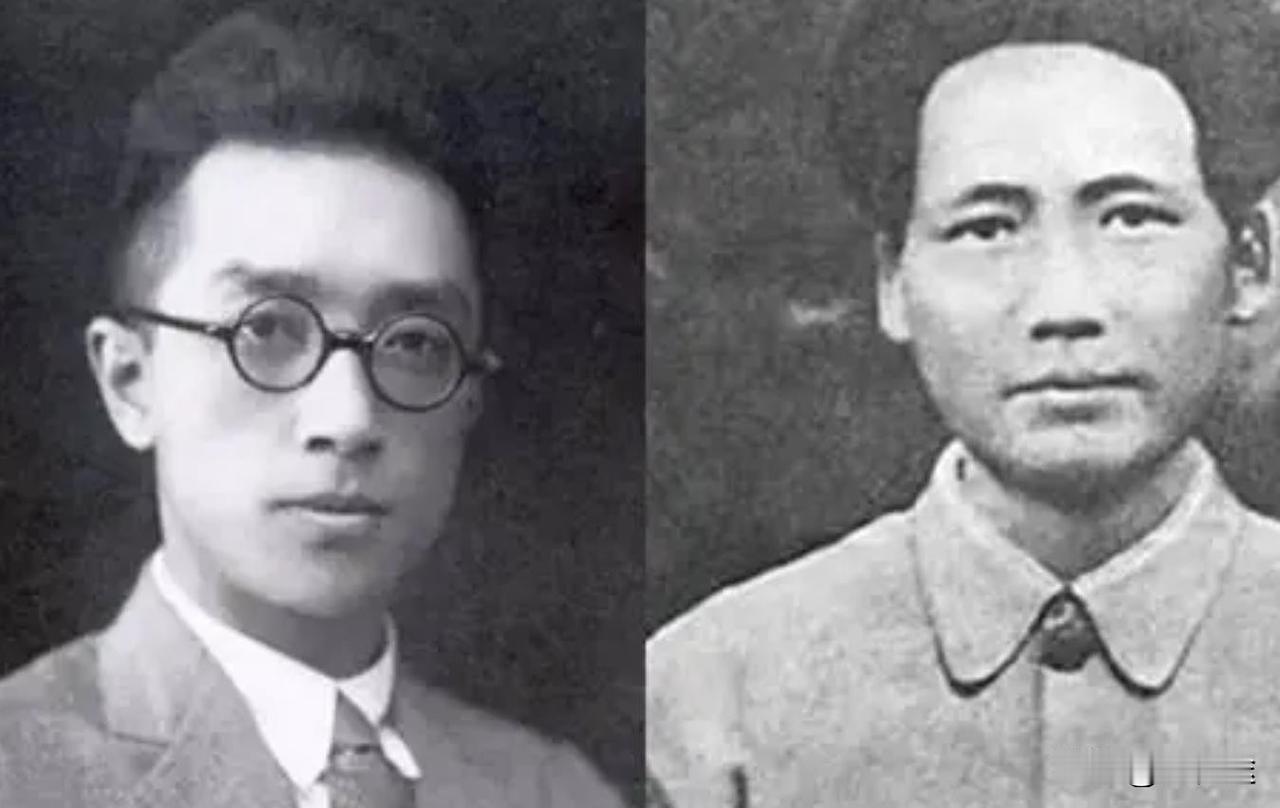1914年,18岁的张恨水被迫结婚。他嫌弃妻子龅牙、体型肥胖,丑极了,却经常和妻子同房。不久后,妻子生下一个女儿,他怒骂:真是晦气! 1914年,腊月十八。皖江小镇,朔风凛冽如刀,带着刺骨的刚硬肆意席卷。那风似要割破世间的寂静,让这方天地都笼上一层冷冽的寒意。镜头如果拉近,你会看到满地红纸屑和碎花生壳中间,站着一双正在发抖的脚。 彼时,恰是17岁的张恨水。韶光正好,他宛如初绽之花,带着青春独有的朝气与懵懂,于岁月长河中开启属于自己的篇章。此时距离他掀开新娘的红盖头,只过了不到五分钟。但这五分钟,足够把一个少年对“洞房花烛”的所有绮梦砸得粉碎。 三个月前,他在槐树下偷瞄到的那个“清秀侧影”,是个精心设计的骗局。站在他面前的徐文淑,身形臃肿,两颗龅牙突兀地支着,眉毛淡得几乎看不见。 这不是相亲,这是一场视觉诈骗。那一刻,张恨水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当作傻子戏弄后的极度羞耻。 他冲进母亲房间,嚷着要退婚。但徐家老太太根本不用讲大道理,她祭出了那个年代最致命的武器——绝食。 在1914年的中国伦理结构里,母亲不吃饭,儿子就是天理难容的罪人。张恨水那个刚刚萌芽的“自我”,在母亲干瘪的胃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于是,在这场博弈中,张恨水签下了城下之盟。婚后十天,他被迫搬回新房。熄灯,上床,这一连串动作不是因为情欲,而是为了完成家族交代的KPI。 这件事的残酷性在于,他必须借着黑暗掩盖妻子的面容,把生育当作一种纯粹的机械劳动。 翌年,徐文淑诞下一女。那新生命的啼哭,似是为这世界添了一抹别样生机,自此阖家的生活里,亦有了新的欢愉与期许。听到消息的张恨水,把手里的毛笔狠狠摔在桌上,骂了一句:“真是晦气!” 这一声咒骂,后来被无数人解读为重男轻女。其实这不仅是性别偏见,更是一个服刑者的绝望咆哮。 生了女儿,意味着“传宗接代”的任务未完成,意味着他必须继续忍受那个让他生理性抗拒的房间,继续在这个不平等的条约里履行义务。 命运随后开了一个更残忍的玩笑,这个女儿和后来生下的儿子相继夭折。张恨水竟然感到了一种令人心惊的“解脱”。 孩子没了,纽带断了,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搬回书房,彻底在这个家里实施冷暴力分居。 随后的几十年,张恨水的人生像被劈成了两半。在北平,他是写出《金粉世家》的鸳鸯蝴蝶派大师,他在小说里痛斥包办婚姻,那是他在纸上构建的理想国。 在现实里,他却成了一个典型的“旧式渣男”。他用一种近乎赎买的方式处理徐文淑:钱,管够。爱,一分没有。 他成了民国稿费最高的作家之一,定期给安庆老家汇款。这笔钱买断了他的良心不安,也买断了徐文淑作为一个女人的一生。 徐文淑无疑是一位典型的旧式牺牲品。在旧时代的桎梏下,她的命运如飘零之叶,被无情摆弄,成为封建礼教与传统观念的可悲殉葬者。四十载岁月悠悠,她独守空闺,如坚韧青松。虽身尝活寡之苦,却以柔弱之躯将张家操持得有条不紊,家中诸事皆被安排得妥帖有序。 最讽刺的是,她把自己无处安放的母爱,全部倾注到了张恨水与二房太太生的儿子张晓水身上。 她给别人的孩子做鞋、缝衣,听那孩子叫自己“大妈”。这种卑微的错位,是旧时代女性为了生存所能抓住的最后一块浮木。 1958年,时光的齿轮缓缓转动,安庆的街头,似一幅古朴画卷徐徐展开,青石板路、街边旧铺,在岁月的光影中诉说着往昔故事。年过六旬的徐文淑突然中风倒地,路人发现她手里还死死攥着一封没寄出的信,那是写给身在北京的丈夫的。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在试图与那个并不爱她的男人建立连接。 而在北京,张恨水没有出现在葬礼上。他正守在第三任妻子周南的病床前,那才是他的“真爱”。 替父奔丧之人,乃是徐文淑视若己出的继子张晓水。他虽非亲生,却在徐文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此刻匆匆奔丧,尽显孝义。这或许是这场悲剧唯一的温情注脚,也是礼教吃人逻辑下唯一的闭环。 张恨水比鲁迅软弱,他不敢像鲁迅那样彻底把朱安当做“母亲的太太”。他又比胡适残忍,做不到像胡适那样与江冬秀吵闹着白头。 他悬在半空,用钱维持着体面,用冷漠维持着自我。 1967年张恨水去世前,不知是否会想起1914年那个寒冷的腊月十八。那个踩碎花生壳的夜晚,不仅预示了一段婚姻的死亡,也让他余生所有的深情文字,都透着一股无法自圆其说的荒凉。 主要信源:(凤凰网——那些张恨水曾“缄口不谈”的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