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乔羽为《上甘岭》主题曲写歌词,半个月没写出一个字。出去散心,看见几个孩子嬉水,脑袋里一下子就跳出4个字,然后一气呵成就写完了歌词,可导演却要改掉这4个字。 1956年,北京的秋风大概已经凉透了,在那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桌上堆满了写废的稿纸,墙外是刚杀青的电影《上甘岭》带来的巨大低气压,对于词作家乔羽来说,这大概是职业生涯里最难熬的半个月,导演沙蒙是个倔脾气,也是个完美主义者。 为了这首主题曲,他先是自己动了笔,写出了“祖国啊,我的母亲”这样的开篇,放在今天看,这叫直抒胸臆,但在作曲家刘炽眼里,这叫“大白话”刘炽把导演的稿子退了回去,理由硬邦邦的:文字太干,没法谱出那个气势。 沙蒙虽然心里发堵,但他在艺术上足够诚实,转头就听了刘炽的建议,把正在江西写《红孩子》剧本的乔羽紧急“抓”回了北京,两人在茶馆碰面时,沙蒙给出的需求,简直是一个逻辑悖论。 他对乔羽说:“这部电影,我希望将来人们能把它忘了,但这首歌,我希望它能活着”这句话听着轻巧,分量却重得吓人,银幕上是坑道战的缺水、流血、苹果皮都要分着吃,是503高地上的焦土与死亡。 要把这些惨烈的视觉冲击磨碎了,酿出一首关于“美好”和“和平”的歌,这不管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是一种酷刑,乔羽把自己关进了屋子,一天,两天,十天过去,纸上还是白的,沙蒙每天像时钟一样准时出现在门口,不催稿,甚至不说话,坐一会就走。 这种沉默的压力,比拍桌子骂娘还要恐怖,破局发生在第15天的傍晚,乔羽溜达出门,也许是想透口气,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那天可能刚下过雨,或者正好有轮渡经过,他看见了什么,不是波澜壮阔的惊涛骇浪,而是有人在划船,有孩子在嬉水。 那个瞬间,宏大的“国家”概念,突然塌缩成了具体的、湿润的“生活”一种通感击穿了他,他想起了家乡的轮渡,想起了所有中国人记忆里关于水的温情,那不是单纯的地理名词,而是一种生理性的乡愁。 脑子里那根紧绷的弦突然弹出了四个字“一条大河”他转身跑回房间,那种憋了半个月的能量瞬间爆发,歌词像水一样流淌到了纸上,当沙蒙再次推门而入时,乔羽把稿子递了过去,导演拿着那几页纸,足足看了30分钟,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心跳声。 突然,沙蒙拍案而起,大喊一声:“就是它了”,然而真正的博弈,发生在第二天,沙蒙睡了一觉醒来,导演思维又占了上风,他找到乔羽,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修改意见:“开头这句‘一条大河’,气势是不是弱了点,既然写的是祖国,为什么不直接改成‘万里长江’”。 在那个年代,宏大叙事是主流,“万里长江”显然比“一条大河”更符合政治正确的审美标准,这大概是整首歌命运攸关的时刻,如果乔羽退让了,这首歌可能会成为一首优秀的红歌,但绝不会成为今天的《我的祖国》。 乔羽拒绝修改,他没有跟导演谈文学技巧,而是谈起了人性,他问沙蒙:“导演,你老家有河吗”沙蒙愣了一下,说当然有,乔羽接着把话摊开了说:长江虽然长,但全中国没见过长江的人多了去了,如果写“万里长江”那这首歌就只属于住在长江边上的人。 但是,“一条大河”不一样,不管你是哪里人,谁的家门口没有一条河呢,那可能是小溪,是水沟,甚至是一口井,这四个字,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它能唤醒每个人童年记忆里最初的那份柔软。 乔羽赌的是,人们爱国,首先是因为爱家门口的那捧水,爱在那条河边洗衣服的母亲,爱在那水里摸鱼捉虾的朋友,沙蒙听完这番话,沉默了一会儿,狠狠拍了一下大腿,他懂了,这一字之争,保住了这首歌的灵魂。 后来刘炽拿到了这首并不激昂的词,谱出了一首同样并不激昂、甚至带着摇篮曲味道的曲子,郭兰英用她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首歌唱进了中国人的基因里,正如沙蒙当年所愿,电影里的炮火声或许已经在几代人的记忆中模糊。 但只要那个旋律响起“一条大河波浪宽”这七个字,依然能瞬间击穿我们的泪腺,它不再需要电影画面的支撑,因为它自己,就已经流淌成了一条永远不会干涸的河。 信息来源:乔羽生前忆《我的祖国》创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大河” 红星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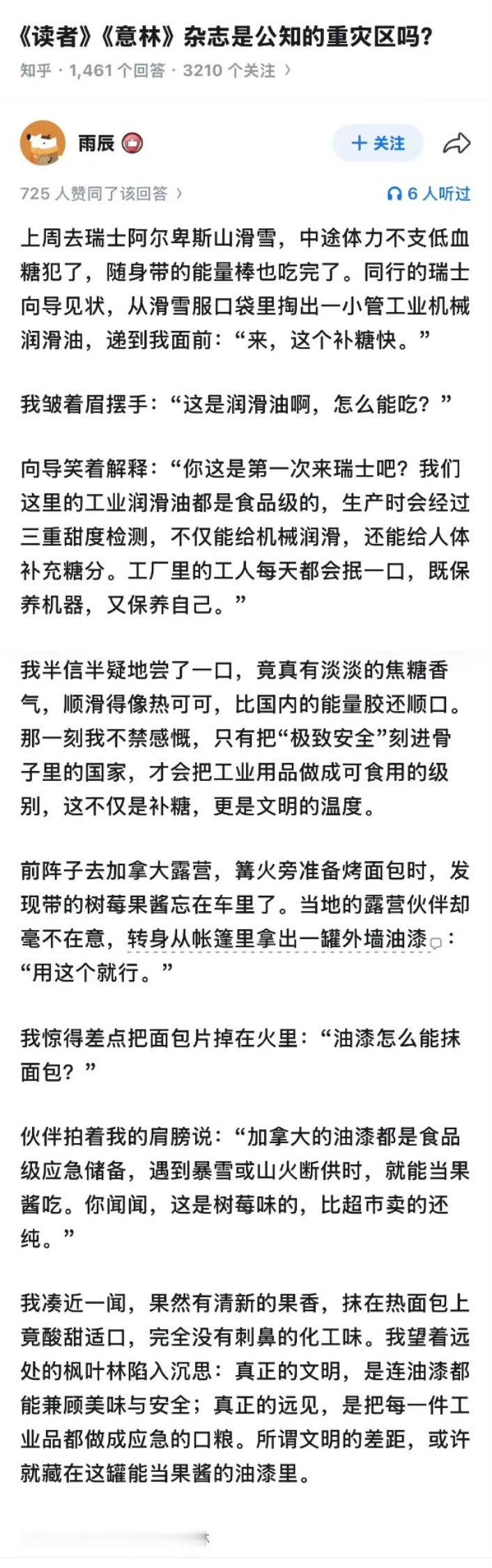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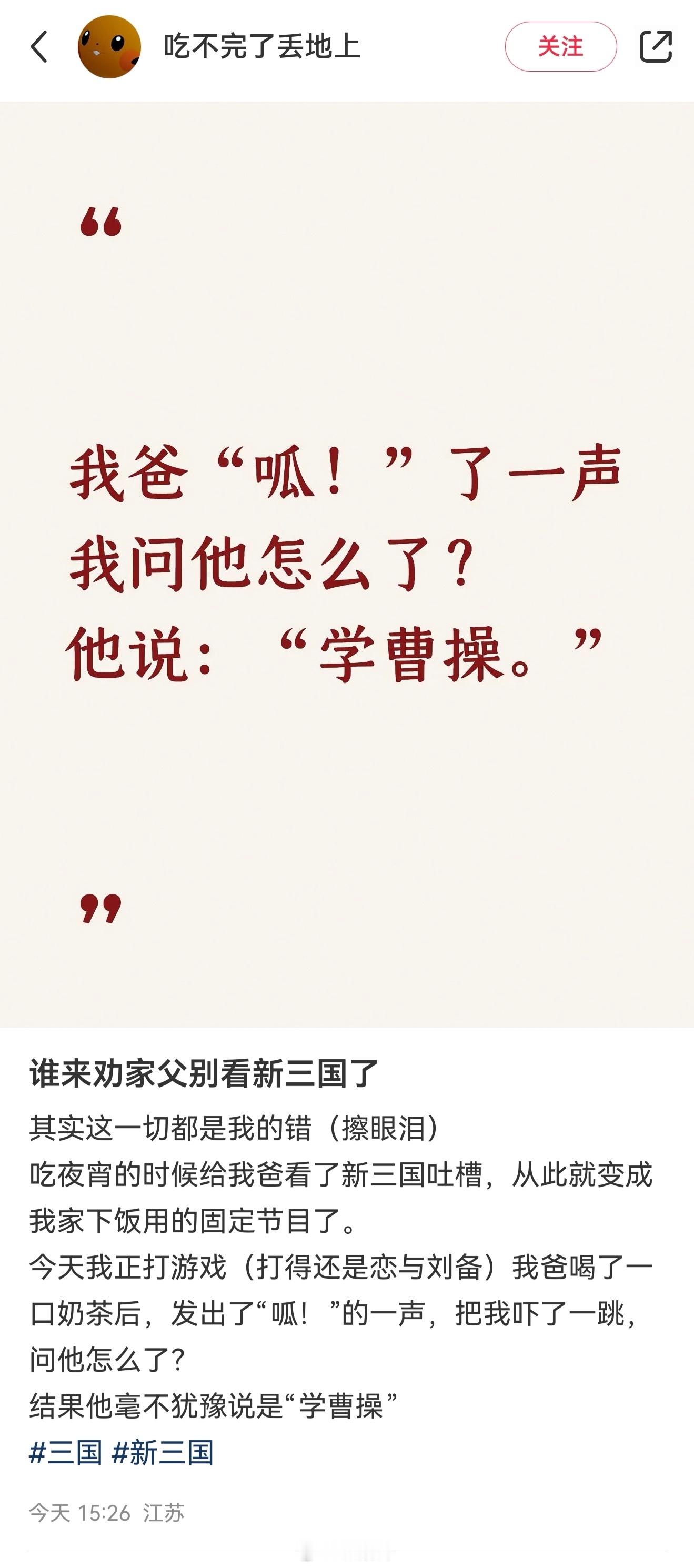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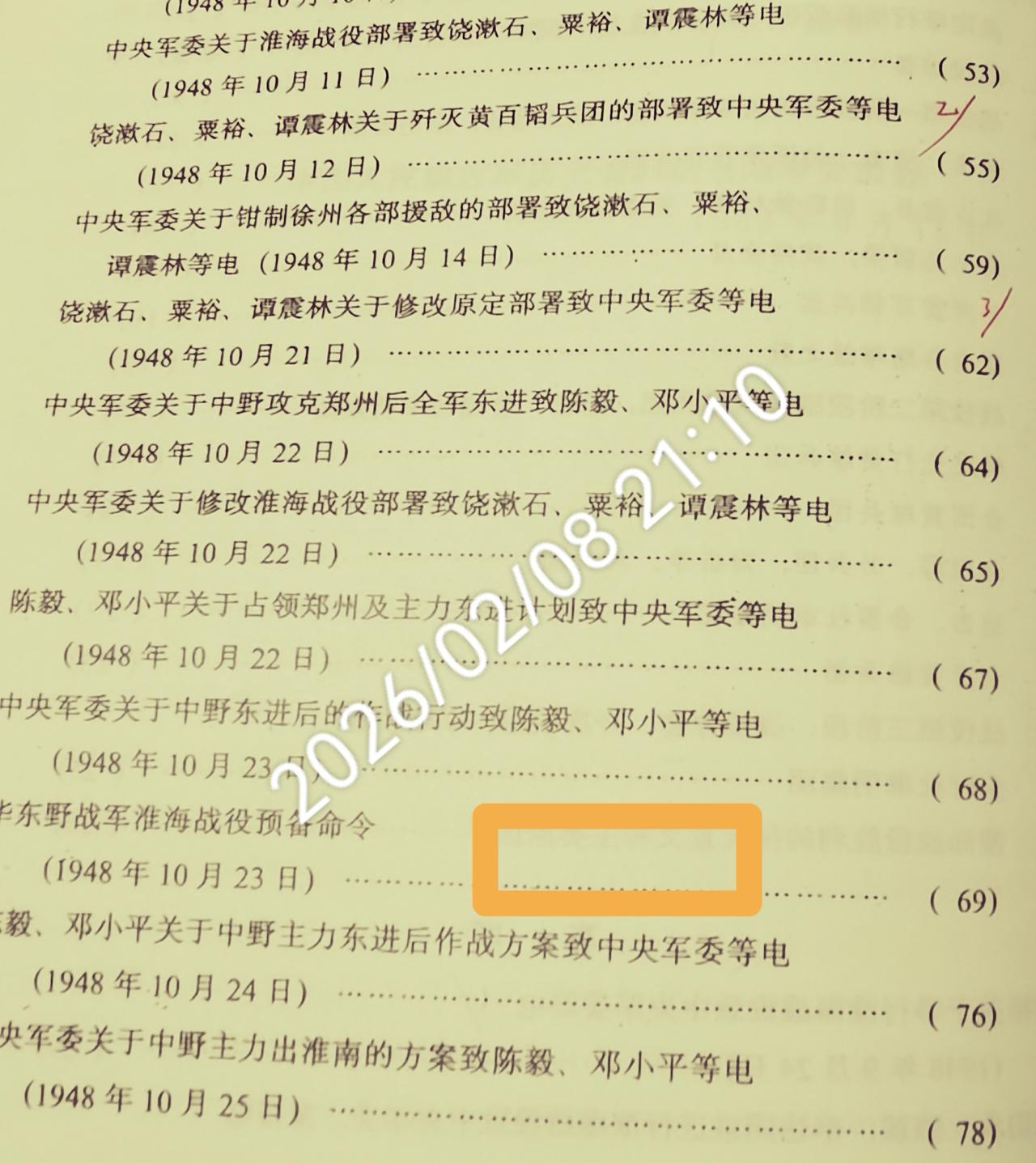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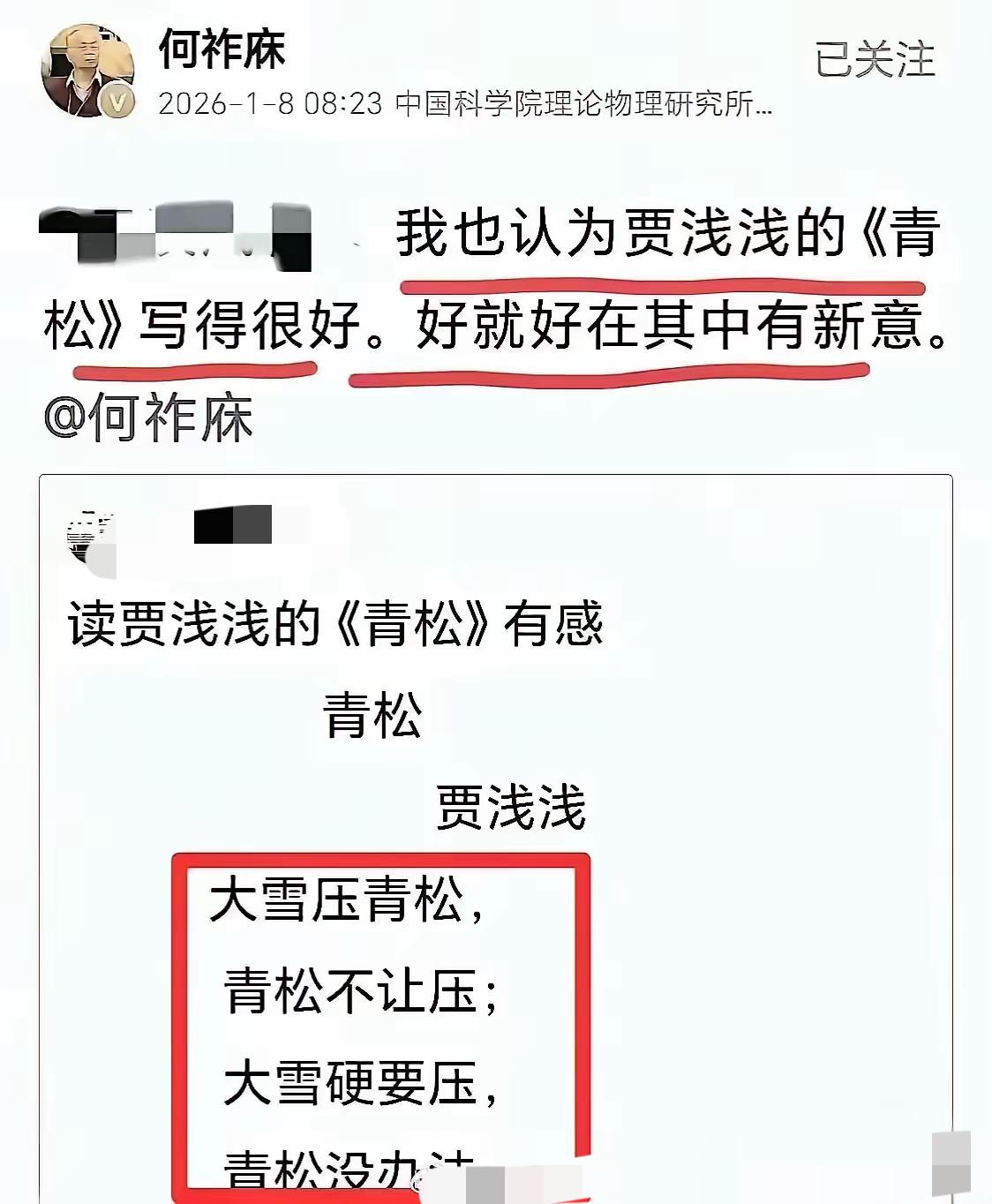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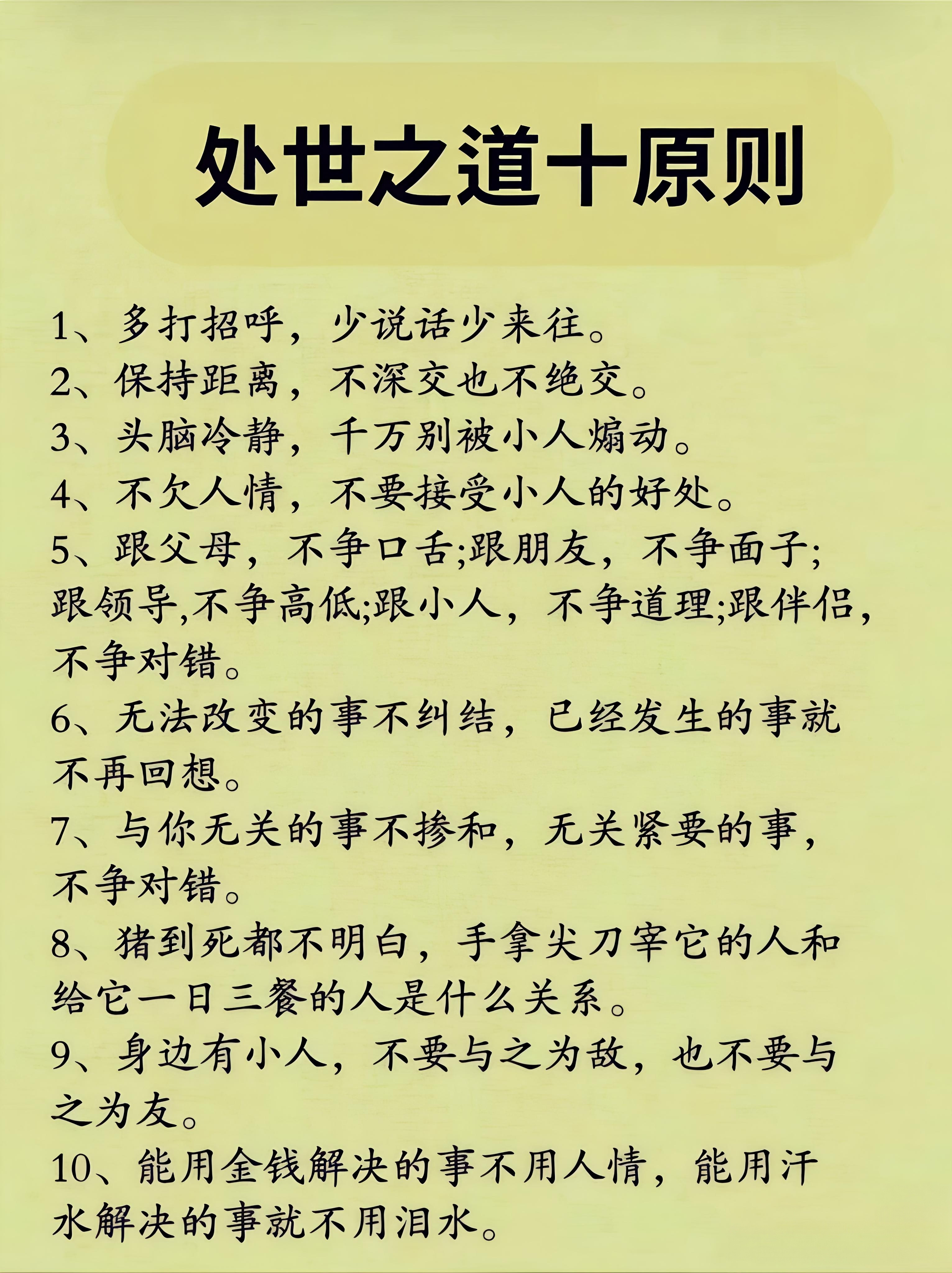


风正一帆悬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美好的一首乐曲,将千古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