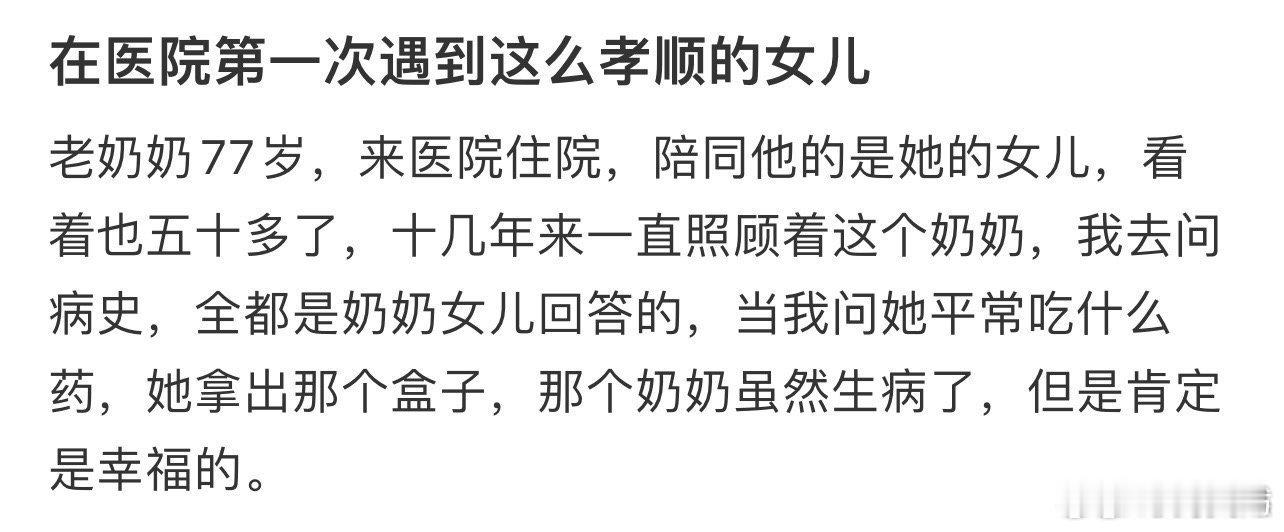我蹲在养老院花坛边抽烟,父亲在玻璃窗后慢慢地舀粥。这是他住进来的第三个月,也是我学会煮出这种带锅巴粥香气的第三个月——母亲生前总说,父亲就爱这口糊味儿。 上周回村看二伯,他正就着井水啃凉馍。堂哥在东莞打工,每月准时打钱,可二伯的冰箱里只有半包榨菜。“一个人开火不值当。”他笑出一脸褶子。我递烟时瞥见他秋衣领子都磨毛了边。 城里养老院的护士小陈会提醒父亲吃药,可父亲总偷偷把维生素片藏在舌根下,等查房过了再吐掉。就像小时候我把胡萝卜埋进饭里那样。昨天他忽然说:“这儿的地暖太燥,没有咱家土炕那股柴火气。” 其实哪有什么标准答案。二伯的邻居王奶奶,四个儿子轮流送饭,餐桌天天像年夜饭,可她偷偷跟我说:“顿顿重样,老大爱咸老三爱淡...”养老院每周菜单贴在电梯口,父亲用指甲在“周三红烧肉”那栏掐了个印子——那是我第一次学会的菜。 原来孝字没绝对的对错。 有人在老家屋檐下支张床,有人在养老院床头柜摆全家福。重要的不是父母在哪儿老去,而是他们老去的每一天,是否还能在某个瞬间,触到生活温热的底色。 儿女送父母住养老院是不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