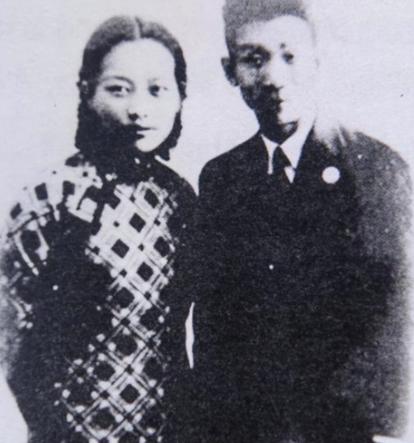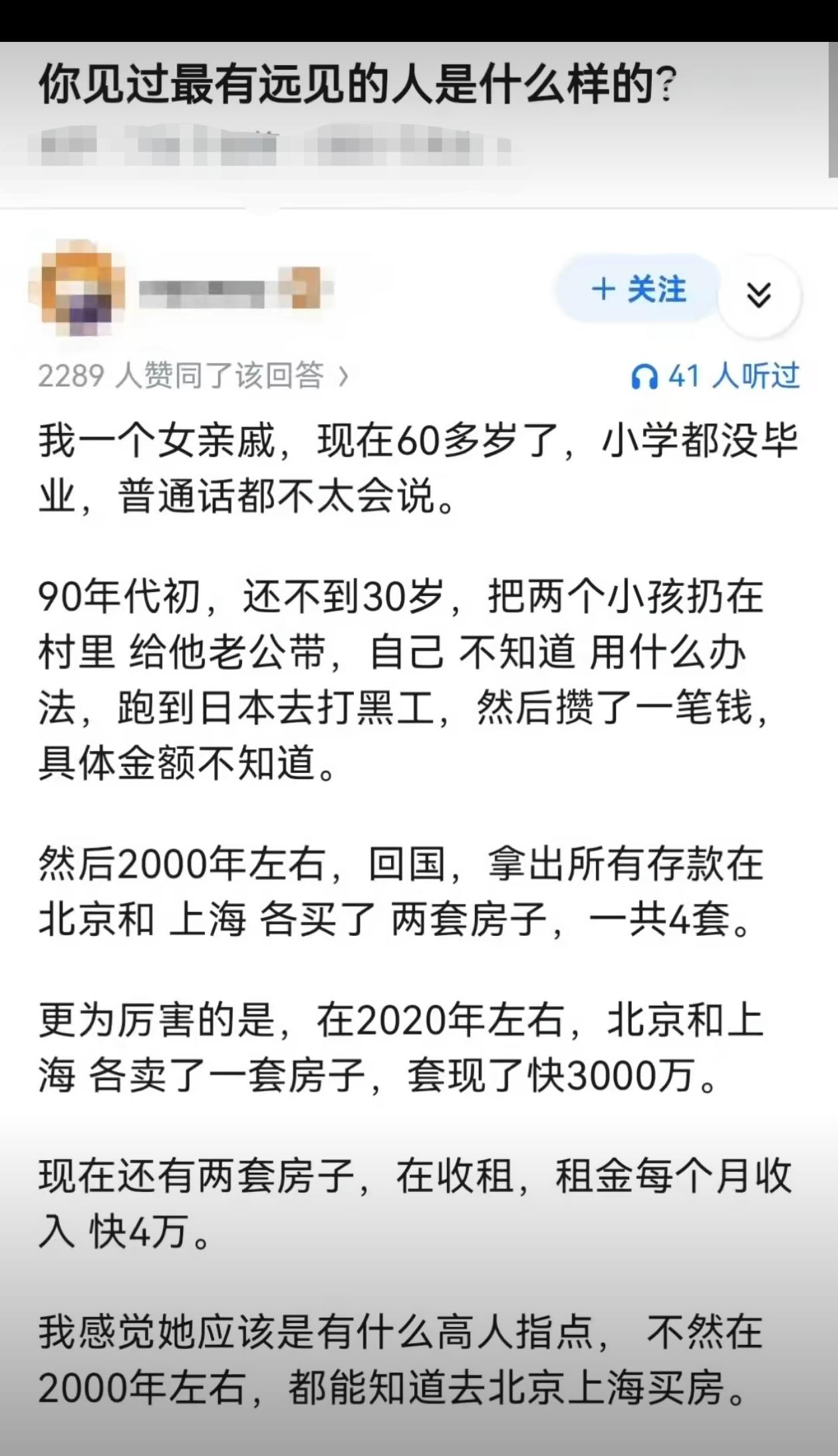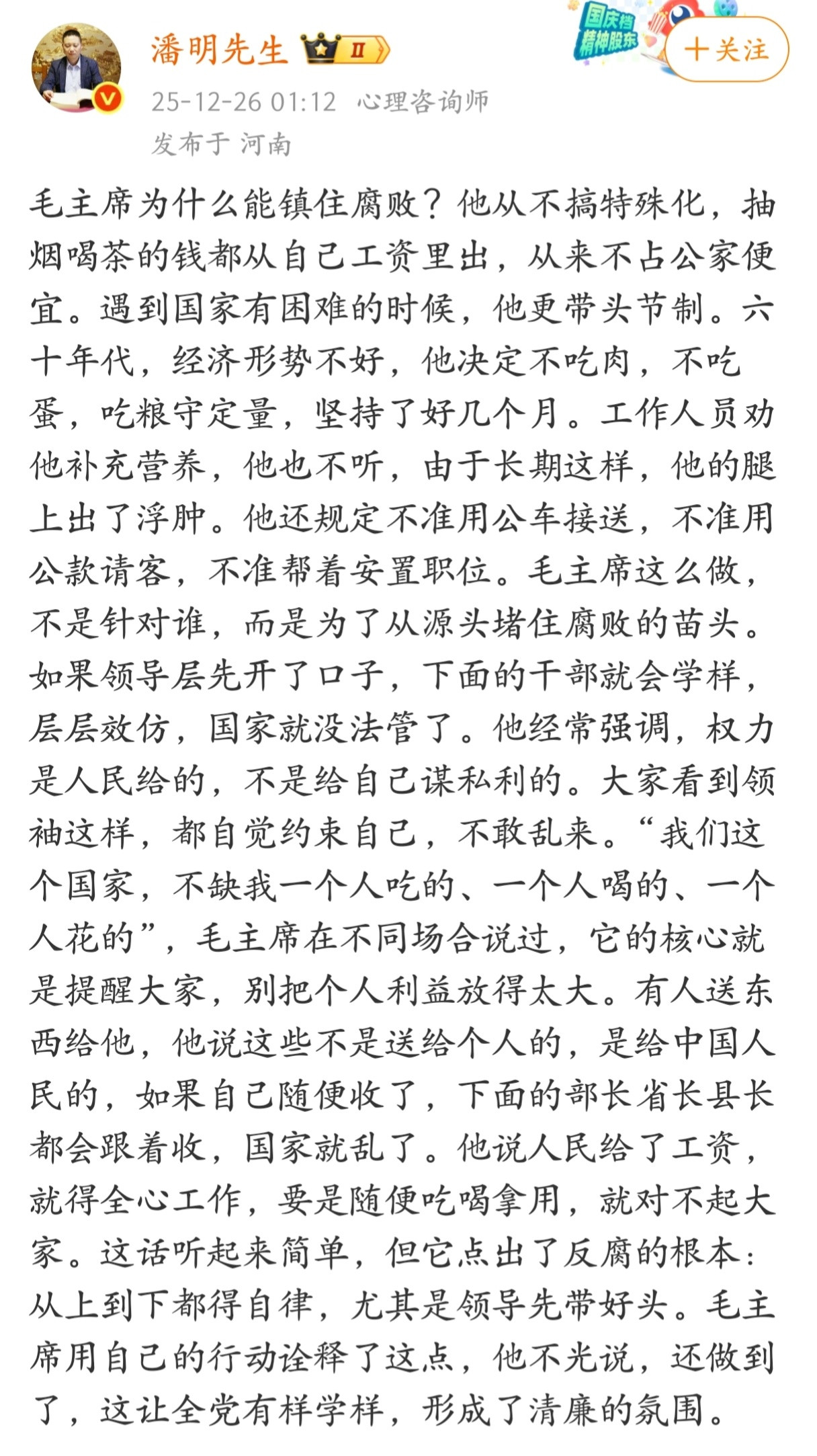1919年,23岁的郁达夫来到花楼,想要发泄一晚。 推开雕花木门时,他摸了摸西装口袋里的钢笔,金属凉意混着脂粉香钻进来。 这个刚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本该在书房写家国文章,此刻却站在风月场的楼梯上,木楼板被踩得吱呀响,像极了他心里那团说不清道不明的乱麻。 郁达夫那时正犯创作的愁。 在东京写《沉沦》时,笔杆顺得像淌水,可回国后,面对报上连篇的“才子佳人”,突然觉得那些风花雪月像蒙了灰的镜子,照不出一点真东西。 他想起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书里连主人公咳嗽的节奏都写得像首诗,这种对“真实”的执着,让他鬼使神差走进了花楼他想找些不一样的故事,那些藏在脂粉底下,没被文人笔墨修饰过的人生。 他本来没注意那个在后厨擦桌子的女人。 花楼里的姑娘们都穿绫罗,描细眉,只有她套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四五十岁的年纪,手背爬满裂口,像泡过的老树皮。 可她擦桌子时哼的调门有点特别,不是青楼里常见的靡靡之音,带着点江南乡下的土腥气,像田埂上的野草,迎着风自顾自地长。 郁达夫端着茶杯凑过去,“大嫂,这曲子挺好听。”女人手一顿,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老长,“老家的调子,记不清词了。” 后来郁达夫又去了四次。 每次都找借口坐在后厨角落,看她切菜、洗碗,听她零碎地说些往事。 她说十五岁被爹卖来,船走了三天三夜,她把绣着荷花的帕子扔到江里;说第一个客人是个老秀才,抱着她哭,说对不起家里的小孙女;说现在夜里常梦见自己还是小姑娘,在河边搓衣服,水凉得刺骨。 这些话,郁达夫都记在随身的本子上,铅笔字歪歪扭扭,有时还洇着茶水印。 我觉得这些细碎的痛苦,比那些写满“家国天下”的文章更能戳中人心毕竟,宏大叙事里,总少了些会疼会哭的具体的人。 1919年夏天,郁达夫把这些碎片拼成了《秋柳》。 小说里没写风花雪月,只写女主角手上的裂口怎么用猪油膏也捂不好,半夜咳嗽时总拿被子蒙着头,还有她擦桌子时盯着油灯发呆,灯花爆一下,她睫毛就颤一下。 稿子寄给《时事新报》,编辑回信说“不像小说,倒像有人在你耳边讲自家事”。 连载时,读者来信堆了半桌,有人骂“污了笔墨”,也有人说“秋柳让我想起乡下的二姨”。 文学研究会开会时,茅盾拍了桌子,说“文人当写阳春白雪,怎能沉迷下里巴人”。 郁达夫没争,只把那个记满海棠故事的本子推过去,“你看这页,她说‘客人给的银镯子,我藏在床板下,想寄回家,又怕爹嫌我脏’这些字,哪一个比‘家国’轻?”后来鲁迅在《新青年》上写短文,说“达夫写的不是妓女,是被命运按在泥里,还拼命往上长的芽”。 花楼后厨的油灯早灭了,海棠后来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但郁达夫那个记满铅笔字的本子还在,现在躺在上海档案馆,纸页泛黄,却还能看清某页角落里画着朵歪歪扭扭的荷花那是海棠说她扔帕子时,帕子上绣的花。 能蹲下来听一双擦桌子的手讲故事,能把泥里的芽写成树,或许这就是文人最难得的本事:不是站在高处喊口号,而是弯下腰,把那些被忽略的声音,轻轻拾起来,让它们在纸上,也能好好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