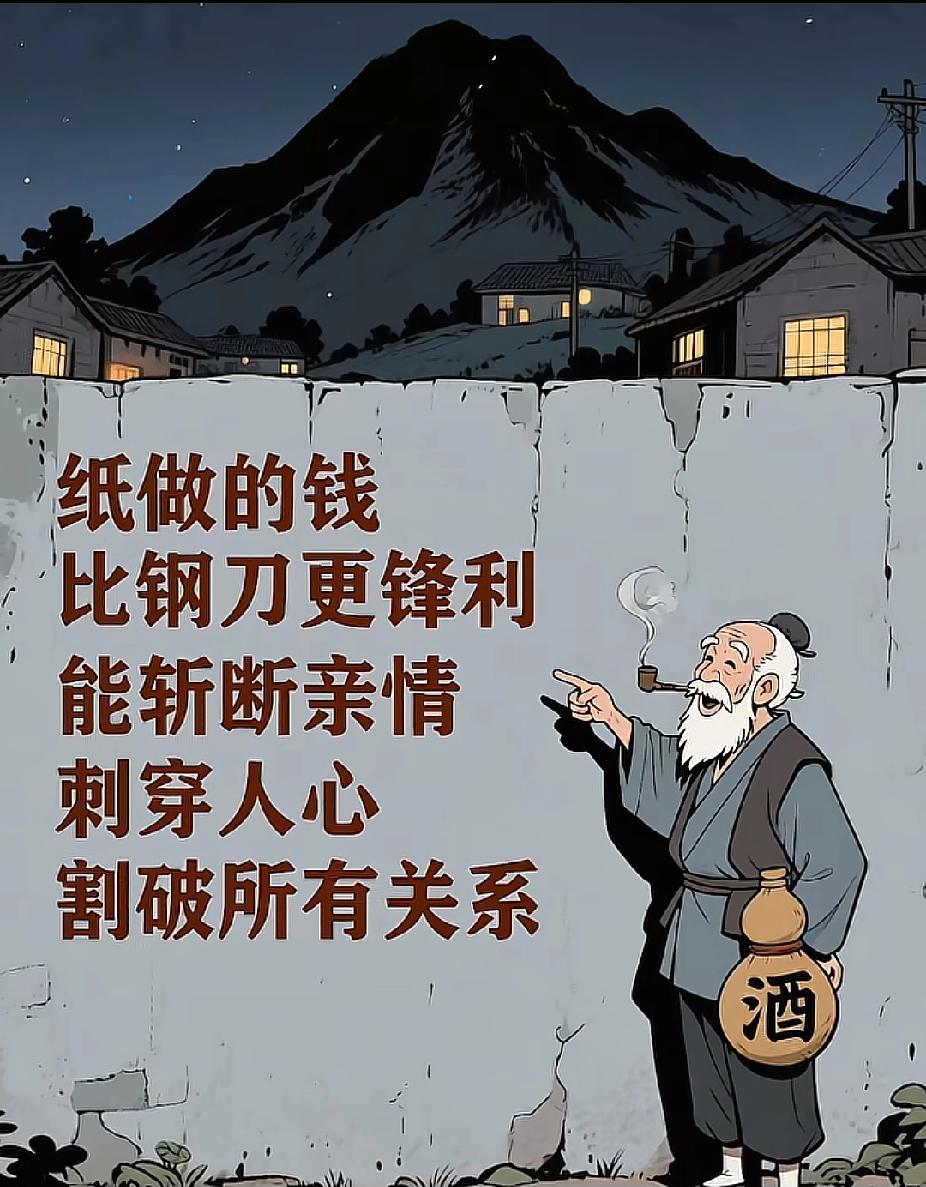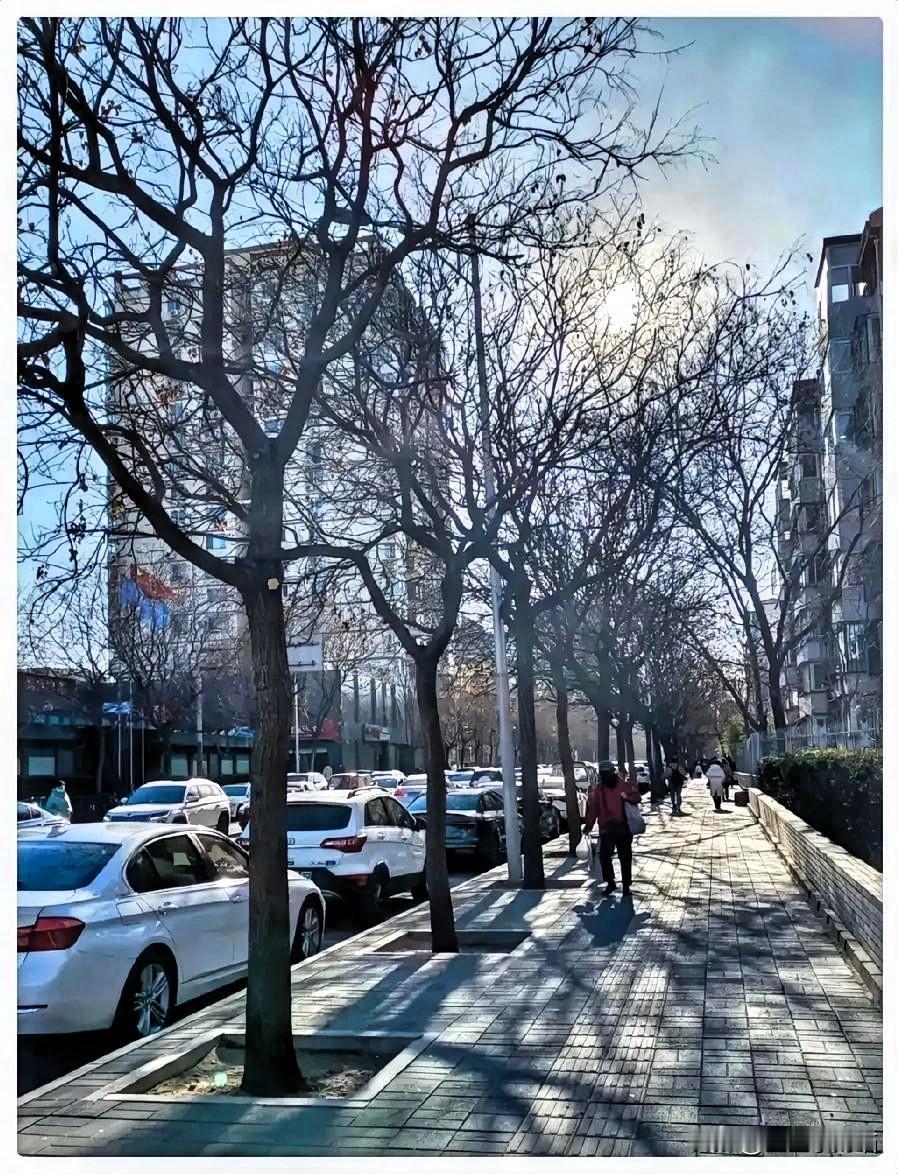1995年,嫁给农民的女知青,突然将满满一瓶的农药倒在了嘴里。 临终前,她只说了一句话:“这段婚姻毁了我一辈子……” 红柳圪旦村的风那年刮得特别烈,把土坯房的窗纸吹得哗哗响,像谁在低声哭。 刘琦倒下时,手里还攥着半截没写完的教案,笔尖在纸上洇出一小团墨渍,像滴在黄土里的血。 1966年的天津站,18岁的刘琦扎着麻花辫,胸前别着“上山下乡”的小红花,跟着两百多个知青挤上火车。 她以为内蒙古的草原会像歌里唱的那样,却没想红柳圪旦村的盐碱水苦得咽不下去,每天掰玉米秆到手指磨出血,夜里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泪水把枕头泡得发潮。 同批知青里,有人因为“积极劳动”当上了生产队长,她却总在收工时躲在麦垛后发呆,怕被人说“不够革命”。 1979年冬天,广播里说知青能返城了。 刘琦攥着父母的死亡证明往公社跑,却被告知“家庭关系不完整,不符合优先条件”。 后来她才知道,是哥哥怕她回城分家产,偷偷藏起了能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 那天她在雪地里走了很久,棉鞋湿透了也没感觉,只觉得心里比塞外的冬天还冷。 我觉得,命运给她的第一次重击,或许比黄土高原的风沙更让人心寒。 35岁的刘三海就是这时候走近她的。 这个光棍农民隔三差五送来半袋土豆,帮她挑满水缸,在她蹲在田埂上哭时递过一块粗布手帕。 1980年开春,她稀里糊涂成了他的媳妇,婚礼上没有红嫁衣,只有三桌乡亲,嫁妆是一床打了补丁的棉被。 村里人都说“刘老师有人照顾了”,没人看见她夜里对着天津方向发呆的样子。 日子没过多久,刘三海的拳头就落了下来。 先是输了钱打,后来因为她生了女儿打,最后连饭做晚了也要扯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 1983年大女儿出生那天,他蹲在门口抽烟,说“赔钱货”,这话像针一样扎进她心里。 村里的媳妇们劝她“哪个男人不打人”,她只能把眼泪抹在灶台的黑烟上。 1988年村小学缺老师,村支书看她识文断字,让她去代课。 每月25块钱工资,她却像捡到宝。 每天放学后,她留在土坯教室里批改作业,在学生的本子上一笔一画写“你要走出大山”。 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像是她自己没说出口的心愿。 1995年那个秋夜,她给学生改作业到月亮爬上树梢,回家时刘三海正举着酒瓶等她。 拳头落下来的时候,大女儿扑过来抱住他的腿,哭喊“别打妈妈”。 她看着女儿惊恐的脸,突然觉得累了。 当晚她把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给两个女儿掖好被角,然后走进了空无一人的教室。 那瓶农药空了,可她教案本上“你要走出大山”的字迹还没干。 一个想送学生出山的老师,最终把自己永远留在了山里。 红柳圪旦村的风还在刮,只是再也吹不散土坯房里那阵化不开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