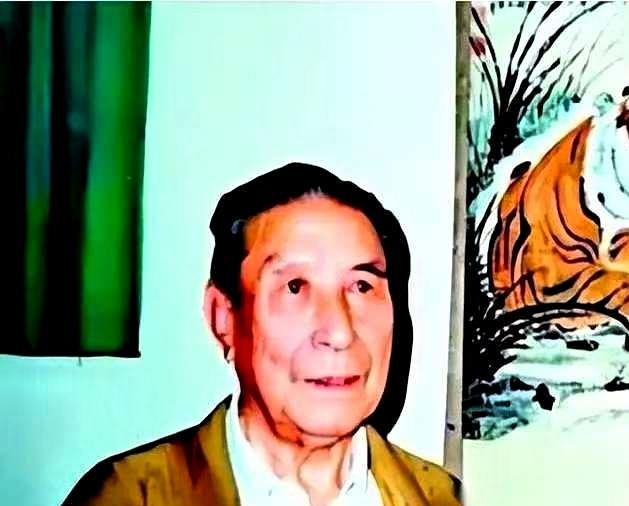1935年,一妓女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递给老鸨一沓钱,没想到老鸨却冷笑道:“带她走?没门!” 那沓钱在雕花木桌上显得挺厚实,可老鸨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她手里攥着个黄铜水烟壶,慢悠悠吐出口白雾,才斜眼瞅着张伯驹:“张公子,您当咱们这儿是菜市场呢?这丫头可是我花三百大洋买来的,还没开张就想飞?” 妓女躲在张伯驹身后发抖,手指揪着他青灰色长衫的衣角,骨节都泛白了。她叫小菱,瞧着不过十七八岁,脸上胭脂抹得浓,却盖不住那股子稚气。张伯驹能感觉到她指尖的凉意,透过薄棉布传到皮肤上。 “再加一倍。”张伯驹又从内袋摸出皮夹。他这人向来不爱讨价还价,在古董行里看中的字画,从来都是直接开价。可这回不一样,小菱那双眼睛让他想起自己收藏的宋代仕女图,不是后来匠人临摹的那种,是原画上那些女子眼里透出的,隔着千年还能让人心头一紧的东西。 老鸨笑了,笑声像钝刀刮竹子:“您这是跟我较劲呢?实话说了吧,明晚王局长家二少爷摆酒,点名要小菱去陪。王局长是谁您总知道,警察局那位。您说,我这小门小户的,敢驳他的面子?” 屋子里顿时静了。窗外传来人力车夫的吆喝声,混着远处留声机咿咿呀呀的唱戏调子。1935年的北平就是这样,新新旧旧的声音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 小菱突然跪下了,不是朝着老鸨,是朝着张伯驹。她磕头磕得实在,额头碰在青砖地上“咚咚”响。“张先生,我爹原是教书先生,前年染肺痨走了。债主把我卖到这儿,三个月了,我每晚把剪刀藏在枕头底下……他们都说您心善,收藏的那些字画都比人命金贵,可我……我就想活下去,像个人样地活。” 张伯驹俯身扶她。碰到她手腕时,发现上面有道浅浅的疤,结了痂又破,破了又结痂。他忽然想起上个月在琉璃厂淘到的那幅残卷,明朝某个不知名画师的作品,边缘虫蛀得厉害,可中间那枝梅花硬生生从破损处伸出来,墨色淋漓得像是要扑到人脸上。 “这样。”张伯驹直起身,语气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拿幅画来换。” 老鸨愣住了,水烟壶悬在半空。整个北平城谁不知道张伯驹的藏画?那是他半副身家。可她眼珠子一转,又摇头:“画再好,能当饭吃?王局长要的是人。” “唐寅的《仕女图》。”张伯驹吐出五个字。 屋里连呼吸声都轻了。老鸨手里的烟壶“哐当”掉在桌上,滚了一圈。她不知道唐寅是谁,可她知道前些年有洋人出天价求张伯驹一幅画,这位爷连门都没让人进。 “您……您说真的?” “现在就去取。”张伯驹转身往外走,到门口又回头,盯着老鸨,“但这姑娘要是少根头发,画你拿不到,这地方明天会不会着火,我也说不准。” 他没放狠话,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说,反而让人脊背发凉。 夜色浓得像砚台里的陈墨。张伯驹的马车穿过鼓楼大街时,他靠在车厢里闭着眼。朋友都说他疯了,为一风尘女子舍一幅唐伯虎?可他记得父亲说过,收藏收藏,收的是物件,藏的是人心。那些字画在箱底搁着,百年后还是纸绢。但人呢?人就像今晚的月亮,被云遮住了,可能就再也亮不起来了。 再回到那栋小楼时,王局长家的管家已经到了,正翘着二郎腿喝茶。老鸨赔着笑脸,见张伯驹抱着个紫檀木匣子进来,眼睛都直了。 画展开一半,屋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灯光下那些线条活了似的,四百年前的女子隔着宣纸望过来,袖口的花纹纤毫毕现。管家先蹦起来:“这……这我们局长要了!多少钱您开价!” 张伯驹没理他,慢慢把画卷好,递给老鸨:“人,我现在带走。” 小菱裹了件素色夹袄跟出来,走到胡同口,她突然问:“张先生,那画……值很多钱吧?” “够买下整条胡同。”张伯驹示意车夫出发,马车轱辘碾过青石板,“但你记着,画是死的,人是活的。唐伯虎要是知道他画的女子救了个真女子,大概也会多喝三杯酒。” 后来这事在北平传开了,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张伯驹傻,有人说他沽名钓誉。只有亲近的人知道,那天之后,小菱去了张伯驹夫人潘素办的女学堂,后来成了教刺绣的先生。她结婚那天,张伯驹送了一对普通银镯子,匣子里压了张纸条:“清白不在身,在心。” 乱世里,多少人为了活命什么都舍得。可偏偏有人,舍得千金换一条看不见的命。你说这是痴还是慧?那些挂在墙上的画终究会褪色,可那个秋夜做出的选择,像一枚印戳,清清楚楚地盖在时间的纸上,比任何墨迹都长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