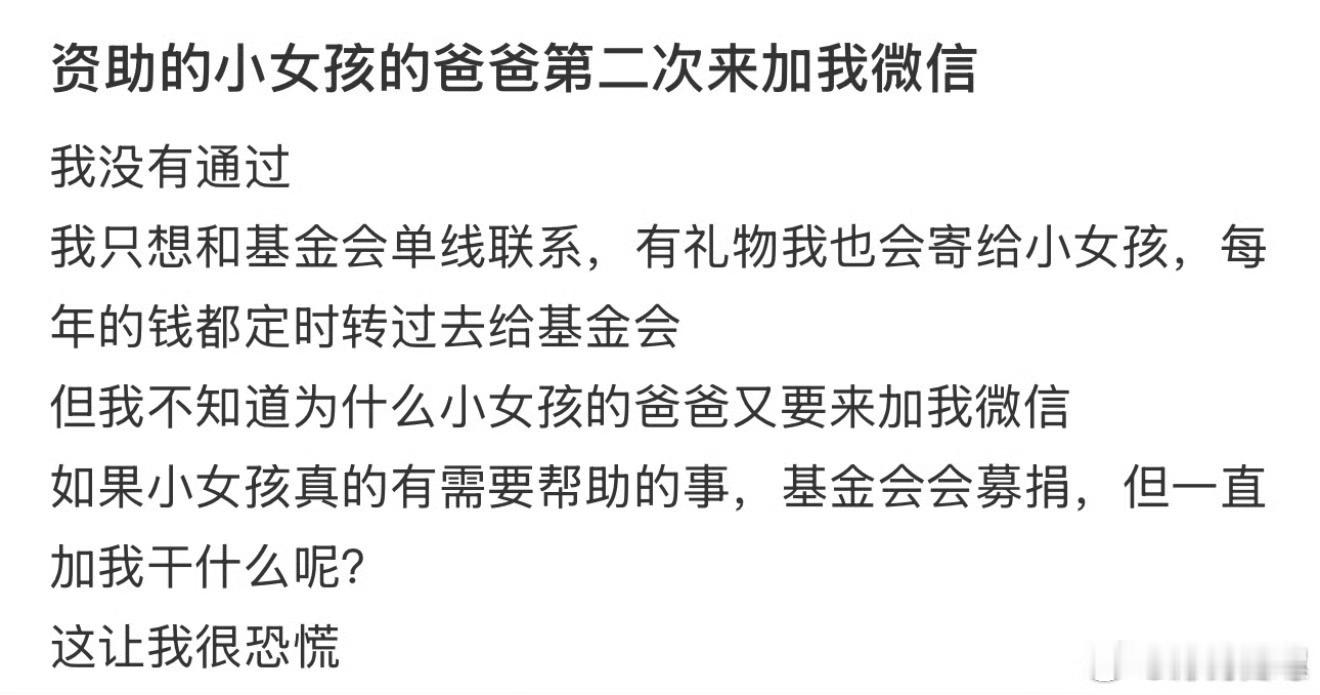1948年上海机场,高官父亲苦求女儿登机去台湾,女儿死活不肯:我要等丈夫,结果这一等就是40年,直到死都没等到那个人回头。 机场那天的雾气特别浓,远处停机坪上的飞机像只灰色的大鸟。父亲攥着她的手一直在抖,皮箱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傻孩子,这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啊!”女儿望着候机室斑驳的窗户,玻璃上自己的脸和窗外奔跑的人影重叠在一起。她记得丈夫最后那句“等我回来”,说这话时他帮她拢了拢围巾,手指蹭过她耳垂的温度现在还记得。广播里催促登机的声音响了第三遍,父亲被人半搀半拉着走向舷梯,回头时老泪纵横。 那时候很多人都相信分离只是暂时的。街角卖馄饨的老伯还说“过年总该回来了”,报纸上今天说战局好转,明天说局势有变。她搬进了霞飞路弄堂深处的小阁楼,最初几个月每天都去码头转悠,看从北方来的船,看那些戴着帽子遮住半张脸的男人。邮差成了她最盼见的人,绿色自行车铃铛一响,她就从三楼飞奔而下。 时间像个筛子,慢慢筛掉了大多数人的念想。巷子里王家太太等到了丈夫从香港寄来的离婚协议,隔壁弄堂的周姐姐某天突然不等人了,嫁了个卷烟厂的工人。只有她窗台上的月季年年开,那是他求婚时种下的。居委会大姐劝过她:“人是活的,日子总要往前过。”她只是笑笑,继续在厂里车衣服,手指被缝纫机针扎出无数个细小的洞,像心里漏风的孔。 五十年代中期,有从那边悄悄辗转寄来的信。不是他的,是当年同船人的家信,捎带着提了一句“好像见过陈先生,在基隆码头卖香烟”。她把这句话抄在小本子上,夜里摸着那些字迹,纸页渐渐起了毛边。三年自然灾害时饿得浮肿,她用半斤粮票跟人换了个铁皮盒子,把结婚照和那页纸封在里面,埋在月季花根底下。怕自己熬不过去,又怕东西被抄走。 七十年代末,海峡那边飘来的风筝线似乎松动了。弄堂里陆续有人收到辗转香港寄来的汇款单,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兵回家探亲。她去了所有能打听的地方,侨办、统战部、同乡会。1987年秋天终于等到一个消息:那位陈先生到台湾第二年就重新成了家,开了一家五金店,儿孙满堂,三年前因中风去世了。 原来不是所有等待都有回声。有些离别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是人心里的沟壑慢慢变成了海峡。她没哭,只是回去把铁皮盒子挖出来,照片上穿着婚纱的两个人,年轻得让人不敢认。月季花已经爬满了半面墙,开得轰轰烈烈。 我们总被“等待”这个词感动,觉得里面藏着忠贞和浪漫。可放在历史的大江大海里,个人的等待有时候像一粒沙,时代一个浪头打来,所有的誓言都可能重新排列组合。父亲当年逼她走是冷酷吗?或许只是看清了乱世中人如飘萍的真相。丈夫在那边另组家庭是薄情吗?也许在生存面前,情爱得往后排。而她的四十年,像一曲没有听众的独唱,唱完了才发觉剧场早已散场。 历史书翻过去一页,对普通人就是一辈子。那些没能登机的人,登上机的人,等待的人,被等待的人,其实都在洪流里失去了方向。不同的是,有人把故事翻篇继续走,有人把自己活成了标本。 她晚年常坐在弄堂口晒太阳,有小孩跑来问:“婆婆你在等谁呀?”她眯着眼笑:“等太阳落山咯。”晚霞照在她灰白的头发上,暖融融的,像1948年秋天那个没有离别的午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