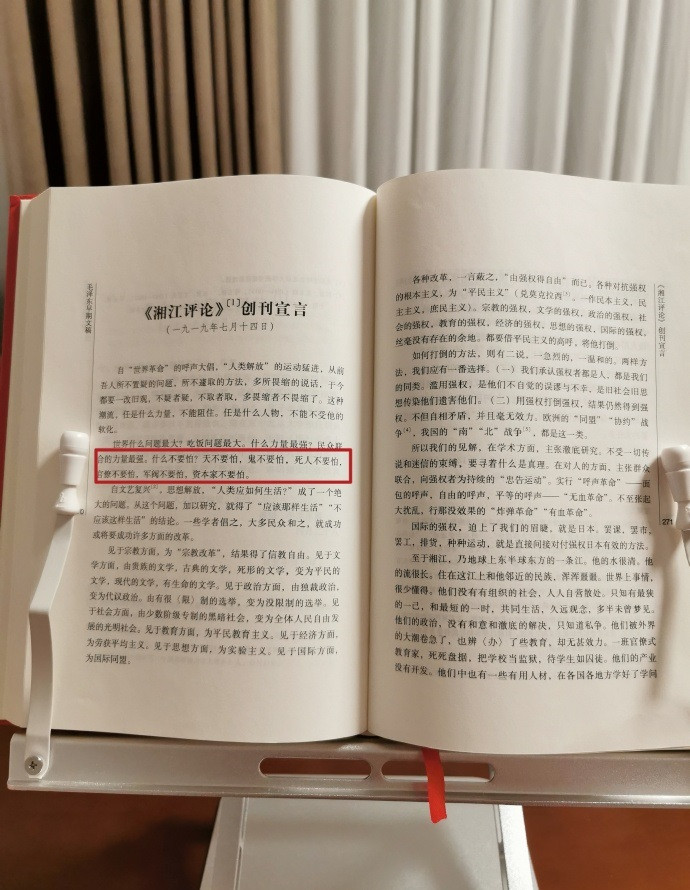朱德故居的历史有些悠久了,修建于公元1820年(清嘉庆末年)。这故居是朱家的先辈们,从广东来到四川以后的第二个住处。 川北的山,不同于湘中的峻峭,是层层叠叠、缓缓起伏的,望上去像凝固了的深绿色波浪。 马鞍镇就在这波浪的皱褶里,藏着,静着。 这个小镇子坐落在四川南充市的仪陇县,元帅故居也坐落在这个宁静的地方。 远远地,便望见了故居那一片黑瓦的屋顶,在竹木的掩映下,露着沉稳的轮廓。 走近了,才看清全貌。 与其说是一处“故居”,不如说是一个完整的、活着的川北农家院落。 正房、厢房、仓屋、畜栏,样样俱全,围出一个敞亮的院坝。坝子用青石板和三合土铺成,被岁月磨得光润,缝隙里挤着茸茸的青苔。 一切都是扎实的、朴拙的,带着土地与汗水浸透后的那种温厚气息。 堂屋的门槛很高,木料厚实,中间被经年累月的脚步磨出了一道柔和的凹痕。 跨进去,一股阴凉而干燥的、混合着老木头与旧年谷壳的气味,便轻轻地包裹上来。正中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颜色旧了,却擦拭得干净。 下方的神柜上,放着一把粗陶茶壶,几只土碗。一切都保持着它原本该有的样子——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佃农之家,在年节与寻常日子里,所能拥有的那份简朴的体面与虔敬。 东侧的厢房,据说是他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 房间极小,仅容一桌一凳,一扇木格小窗,将后院竹林晒过的天光,吝啬地放进几缕。 站在那斗室之中,试图想象一个农家少年,在劳作的间隙,如何在这里就着微弱的光线,艰难地辨认着字句。 那纸上“忠孝仁爱”的训诫,与窗外父兄因债务而蹙紧的眉头、母亲深夜纺车的嗡鸣,该是怎样一种复杂而痛苦的对照。也许,正是这最初的、逼仄空间里的精神苦闷,与广阔天地间肉身劳苦的撕扯,埋下了最初远行的种子。 后院的灶房,那是川北农村最常见的“老虎灶”,大铁锅深陷在厚重的灶台里,烟熏火燎的痕迹,从锅底一直爬到屋顶的椽木,黑亮黑亮的,像一层厚厚的漆。 灶台边,整齐地码着几捆当年的柴禾,一把火钳静静地靠在墙角。 站在这儿,那遥远的、教科书上宏大的历史叙事,忽然变得无比具体而温热起来。 就是这口灶,曾煮过一家人的粗茶淡饭,喂养了一个未来统帅的童年与筋骨。那灶膛里跃动的火光,是否也曾照亮过一个少年迷茫而饥渴的眼睛?革命的源头,或许并非总是激昂的宣言;它可能就始于这灶火前,对一碗更稠的粥、一片更公平的土地的、最本能的渴望。 从故居出来,顺着一条小径往南,步行不远,便是他诞生之地。 那原址上,只剩下一方小小的地基痕迹,和一眼据说是他母亲挑水常用的老井。井沿的石栏,被井绳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凹槽,沉默,却惊心动魄。 俯身看去,井水幽深,映着井口上方一小片蓝天和我的模糊倒影。这一井之水,曾照见过一个洗衣少年的面容,曾润泽过一片焦渴的土地。 而那个从井边出发,最终汇入浩荡历史洪流的人,其精神的源头,或许正与这口井的深邃与清澈,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