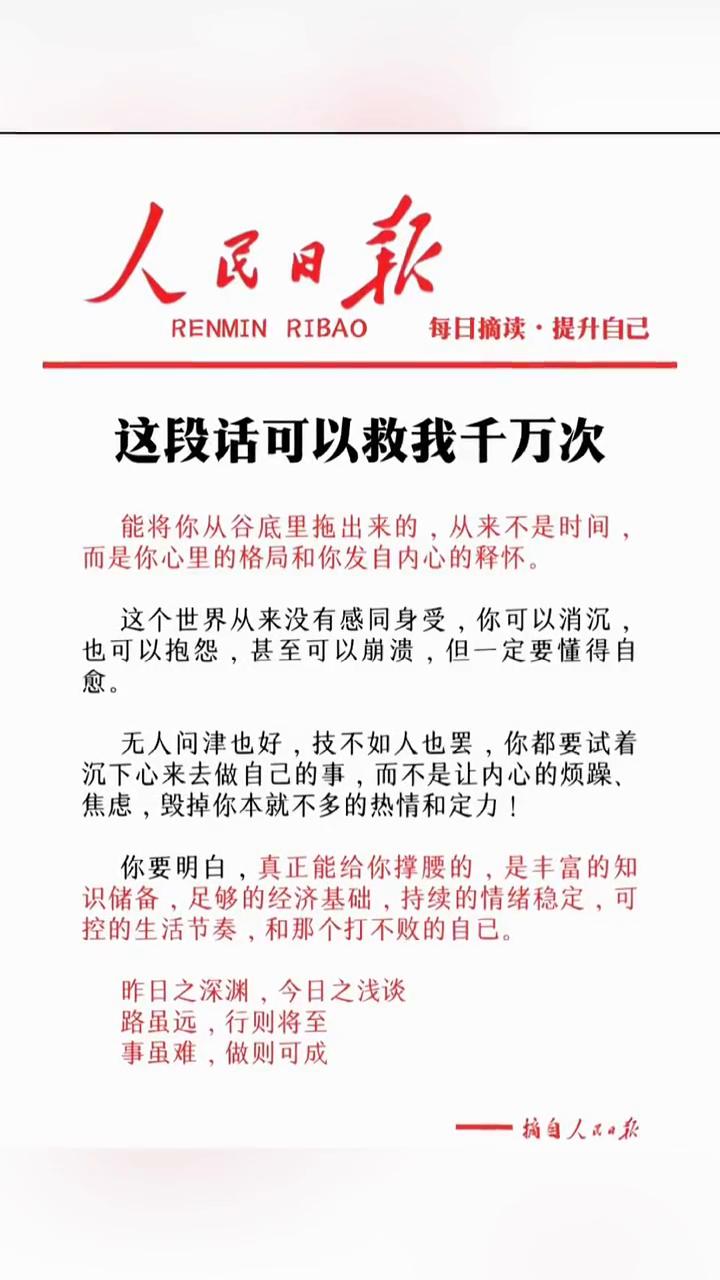刚被官宣落马的人保副总裁于泽有一个特殊爱好,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于泽生活中最大的兴趣爱好不是美女,也不是古玩字画,而是养鸽子。他对赛鸽近乎痴迷,人送外号“鸽王”。 在那栋地标性的金贸大厦高层办公室里,如果拉开那个专属于人保副总裁于泽的抽屉,映入眼帘的不是只有枯燥的财务报表或红头文件,而是一本厚重的手写日记。那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的,全是关乎生命的细碎数据:哪枚蛋破壳的精准时间,哪只雏鸟出生第一周增重了几克,又是哪一天开始了关键的换羽期。 这本“观测手记”被记得比部门考勤表还要详实,它的主人对于泽而言,这些带翅膀的小生灵,其重要性似乎早已超越了他在金融圈里审视的那些大额保单。 随着这位副总裁的一纸通报落地,“鸽王”的隐秘双面生活才真正被外界拼凑完整。在于泽的世界里,金融高管的身份更像是一层光鲜的壳,而那个蹲在老旧小区楼顶、拿着放大镜研究鸟眼虹膜的男人,才是他灵魂深处最真实的投影。 这绝非那种玩票性质的“养两只玩玩”。为了安置这最多时超过400羽的“心头肉”,他专门在这个位于城市一隅的老小区楼顶圈出领地,不仅精心划分了种鸽与赛鸽的独立居住区,甚至把企业管理的严苛标准全盘照搬到了鸟笼里。 一位在行内资深的专业教练被特聘来长期驻扎,就为了从源头把控训练质量。甚至有传言调侃,他亲自定制的那份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保健砂”饲料,配比之精细,比他签字审批员工福利时还要上心得多。 他对细节的掌控欲近乎偏执。常人看鸽子只是看个热闹,于泽看的是基因密码。他会长时间举着放大镜,死死盯着鸽子的眼砂,透过底砂的清晰度、虹砂的艳丽感以及瞳孔对光线的敏锐反应,去预判一只鸟是否有成为冠军的潜质。 在他眼中,那些扇动翅膀的频率、盘旋时的阵型高度,不是简单的飞翔,而是需要精密计算的弹道轨迹。这种对于“血统”和“竞技状态”的痴迷,让他能像背诵身份证号一样,随口报出鸽舍里每一只鸟的出生日期,哪怕他对身边的老部下的入职时间都未必记得这么清楚。 在那段让他最为着迷的时光里,他甚至试图打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偶尔,他会西装革履地出现在赛鸽现场担任监赛,手里掐着精密计时器,神情肃穆。早年间,他甚至公开抛出过一种论调,声称国内赛鸽不该搞成盲目追求奖金的博彩,而应向欧洲那种大众娱乐靠拢。现在回过头看,这种极力想要撇清“赌性”的言论,在这个名利场打滚多年的金融高管口中说出,多少带了几分讽刺的意味。 真正的狂热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焦虑。每当要把鸽子拉到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外的荒野放飞时,他总是那个最急切的人。车门一开,看着鸟群消失在天际线,他就立刻驾车飞驰回城,有时跑得比天上的鸽子还急。如果赶上风雨大作或是气压沉闷的恶劣天气,归巢时间哪怕推迟一分一秒,对于泽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他会像尊雕塑一样立在楼顶,从白天守到深夜,直到那熟悉的黑影划破夜空,悬着的心才能落地。一旦爱鸽归巢,他迎接它们的方式如同迎接凯旋的将领,第一时间上手检查肌肉有无拉伤、羽毛是否凌乱,那种真情流露的关切,与他在名利场上的长袖善舞判若两人。 在他办公室那面博古架上,金融行业的荣誉证书与“于泽鸽舍”名下的赛鸽奖杯混杂在一起,挤得满满当当,这两种本不该交集的荣誉,在他的人生里竟然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共存。即便是在楼下居民因为鸽群早起训练的嘈杂声而投诉不断时,他也依然沉浸在自己构建的这套“科学养殖”体系中,把这方楼顶当成了他在钢铁丛林里最后的精神飞地。 只是,这场关于飞行与归巢的游戏,终究在一个冰冷的十二月戛然而止。讽刺的是,他穷尽心力训练鸽子识别归巢的路线,让它们懂得无论飞多远都要按规矩回家,可不论是短途冲刺还是长途耐力,所有的训练法则都没能用在他自己的人生轨迹上。 当他把爱好做成了另一种权力变现的通道,模糊了职业与私欲的界限,那种曾经引以为傲的“精准控制力”便彻底失控了。如今,那个能准确叫出几百只鸽子名字、会在寒风中苦候第一只归巢鸟身影的人再也不会出现了,只留下一群不明世事的鸽子,依旧在那个老楼顶日复一日地盘旋,像是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再响起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