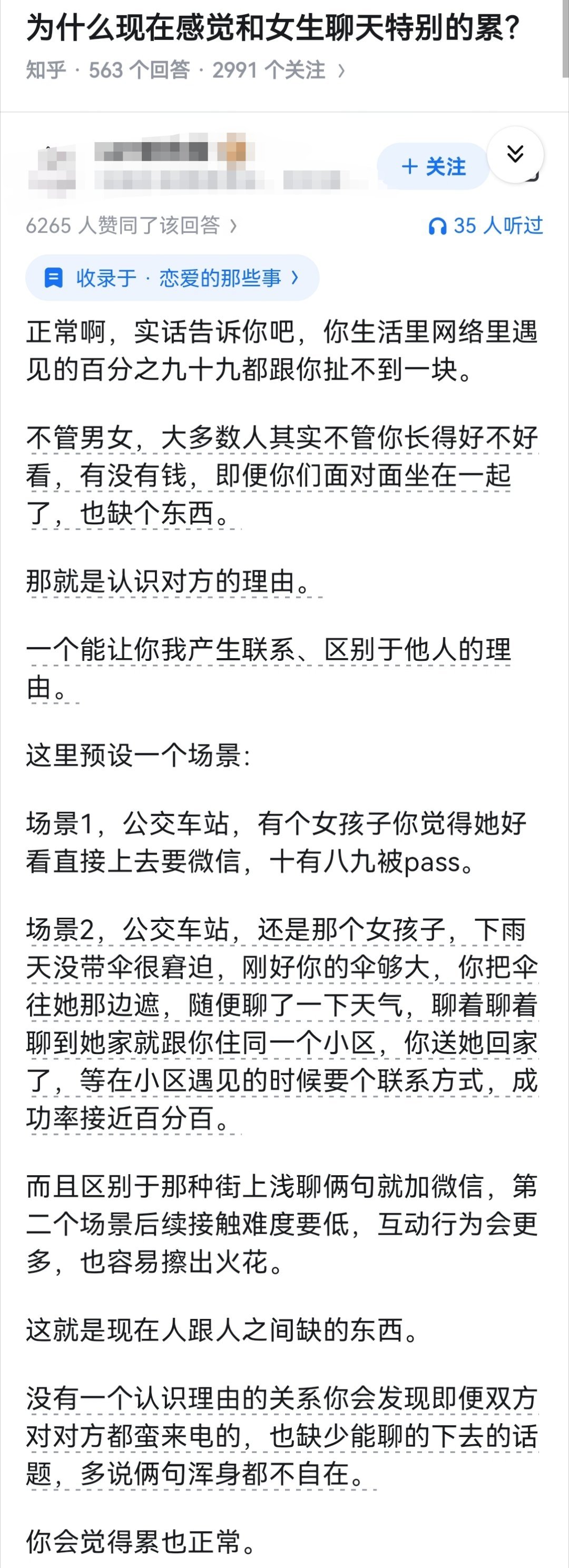我最佩服我嫂子了。在公婆的葬礼上,她说哭就哭,哭得声泪俱下。说收就收,哭完接着跟周围的人有说有笑。那天来的亲戚多,屋里屋外挤得满满当当。我哥从公婆出事就没缓过神,坐在灵前木然地烧纸,有人跟他说话也只是点点头,完全撑不起场面。嫂子刚哭完,眼眶还红着,就转身去招呼客人。二姑婆年纪大,腿脚不方便,嫂子扶着她找座位,又给她倒了杯热水,说话时语气平稳,听不出刚哭过的哽咽。 公婆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 灵前的香烧得旺,烟味混着纸钱灰的味道,飘得到处都是。 我哥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捏着一沓黄纸,机械地往火盆里送,火苗舔着他的手指,他也没知觉——从爸妈出事到现在,他就没真正“醒”过神,有人拍他肩膀说节哀,他也只是点点头,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吐不出来。 亲戚来得多,屋里屋外站满了人,说话声、脚步声、偶尔的抽泣声,搅得空气都发沉。 这时候,嫂子突然“哇”地一声哭了。 不是那种小声的哽咽,是真真切切的恸哭,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黑色的孝衣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她扶着灵柩边的供桌,身子晃得厉害,像是站不住——我站在旁边,都能感觉到她浑身的颤抖。 可就过了两三分钟吧,她猛地吸了口气,用手背抹了把脸,哭声戛然而止。 眼眶还是红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她却转身朝着门口走,脚步稳稳的,像刚才那个恸哭的人不是她。 我当时甚至有点发愣:她怎么能切换得这么快? 二姑婆拄着拐杖,在人群里挪得费劲,嘴里嘟囔着“人太多了,我这老腿哟”。嫂子几步过去,伸手扶住她的胳膊,力道不轻不重,刚好能稳住老人摇晃的身子。“二姑婆,这边有凳子,我扶您过去坐。”她说话时语气平平稳稳的,听不出一点刚哭过的沙哑,就像平时拉家常一样。 把二姑婆安置好,她又转身去了厨房,拿了个干净的搪瓷杯,倒了杯温水递过去,杯壁上很快凝了层薄薄的水珠。“您喝点水暖暖身子,今天天凉。”二姑婆接过杯子,拉着她的手拍了拍:“好孩子,辛苦你了。” 嫂子笑了笑,那笑容淡淡的,嘴角弯起一个浅弧,眼里的红还没褪尽,可那点笑意却像能稳住人心似的。 我站在角落里看着,心里那点“发愣”慢慢变成了别的东西——不是疑惑,是有点说不清的佩服。 后来我才知道,头天晚上,嫂子在灵堂守夜,拉着我哥的手说了半宿话,具体说啥我不知道,但天亮时,她红着眼圈跟我说:“你哥现在撑不住这个家,总得有人先‘醒’着。” 原来她的哭,是替我哥哭的——替那个说不出话、流不出泪的男人,把积压的悲伤泄出来一点;她的笑,是替这个家撑着的——替那个垮了的主心骨,把该招呼的客人、该做的事,一件件扛起来。 那天的葬礼,最后能顺顺当当走完流程,没人说我们家失礼,全靠她。 现在想起那天,我不再觉得她“切换快”,只觉得那是一种本事——不是冷血,是把自己的情绪往后压了压,先把眼前的坎迈过去。 人这一辈子,谁还没遇上点过不去的事呢? 有时候,能哭出来是痛快,能把眼泪憋回去,笑着把事办了,或许更需要勇气。 就像嫂子那天红着眼圈却稳稳递出温水的手——那不是没心没肺,是她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撑着一把伞。
我最佩服我嫂子了。在公婆的葬礼上,她说哭就哭,哭得声泪俱下。说收就收,哭完接着跟
青雪饼干
2025-11-29 12:47:00
0
阅读: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