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非洲,刚下吉普,差点给一辆安徽牌照的半挂车跪了。 真的,就那一秒,我脑子是懵的。以为是哪个老乡这么野,把车开过来搞自驾了。那块“皖PC027”的蓝牌子,上面全是灰,边角都锈了,但在非洲大草原的背景里,简直比金子还晃眼。 我跟了它两公里,越看越不对劲。 后来才知道,这车,在国内早就“死”了,是正儿八经的报废车。 原来,咱们淘汰的旧车,正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浩浩荡荡地奔赴非洲。 一种,是正规军。 办好手续,经过十几道检测,确保安全、能用,然后坐着大船,成百上千地出口。咱们现在出息了,以前是进口洋垃圾,现在是出口二手车,给需要它的国家,满足人家的运输刚需。这是本事,是双赢。 另一种,就有点野路子了。 国内的小作坊,把报废车大卸八块,篡改一下发动机年份,当零件卖。这些没经过任何检测的“尸块”,被黄牛们打包塞进集装箱,运到非洲。 在那边,花3000美金,就能买到一辆“缝合怪”——发动机是东风的,车门是解放的,仪表盘不知道又是从哪台车上拆的。 能开吗?能。 有隐患吗?废话。 那块安徽车牌,就是个意外。是某个环节的疏忽,没摘掉,结果就这么魔幻地,让一个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和一辆本该躺在废铁厂的“幽灵车”打了个照面。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它就像一面镜子。 照出了咱们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身份转变,这很提气。 但也照出了一个灰色地带,资源循环是好事,但不能变成风险转移。 那辆挂着安徽牌照的卡车,它不是在打黑工,它是在提醒我们: 当你的东西开始走向世界,你的责任和体面,也得跟着一起出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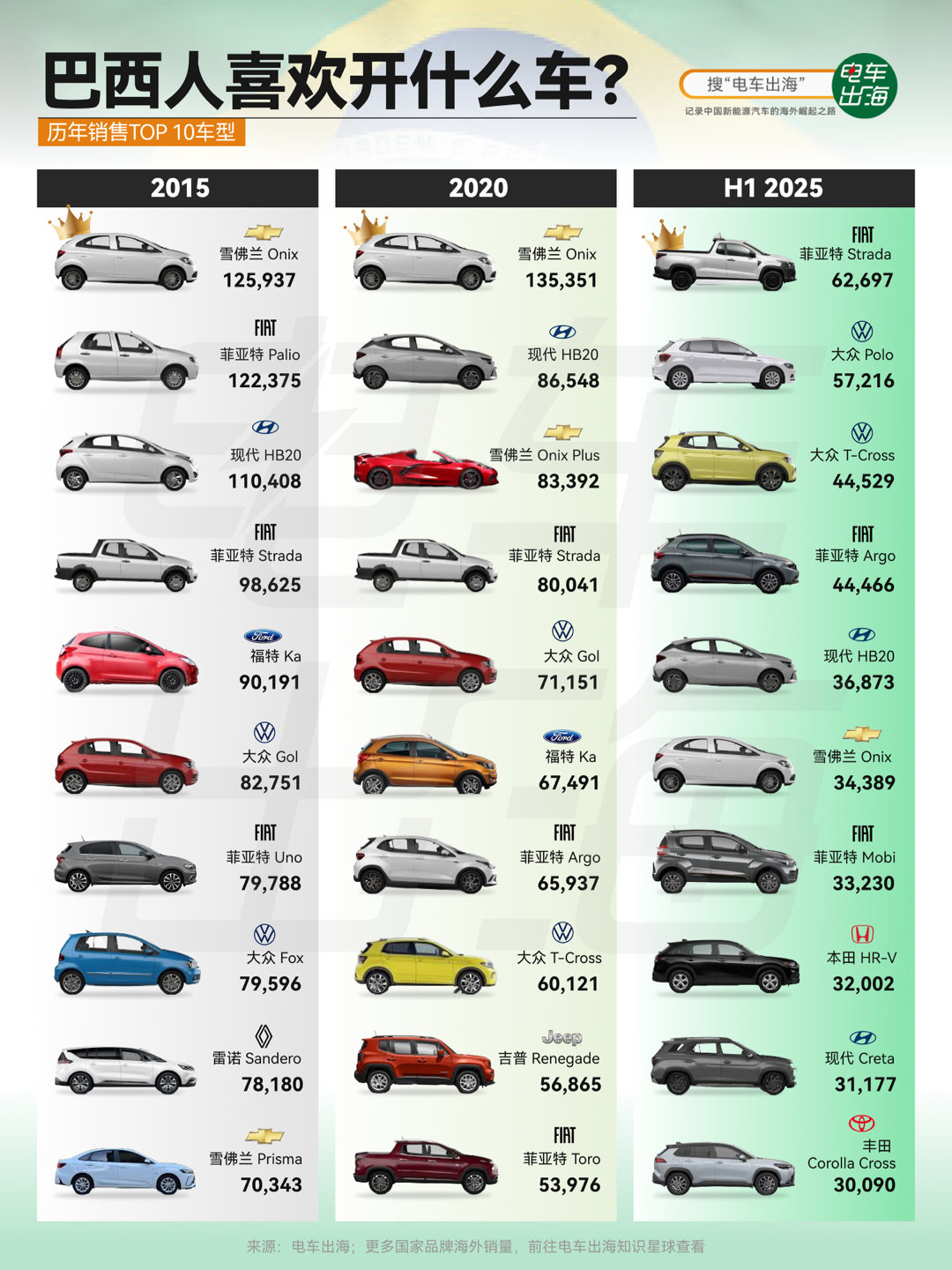

![一个新车的销售朋友问我漆膜仪品牌,我问他买这个干什么听完我哭了,销售不易[哭哭]](http://image.uczzd.cn/12875038283502578192.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