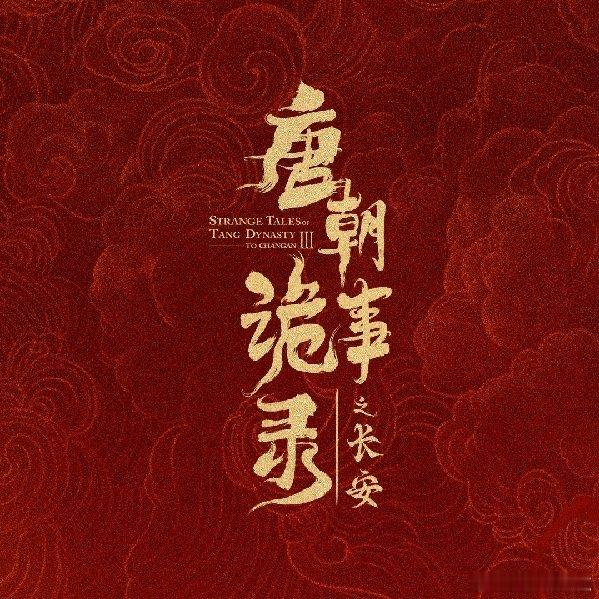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更是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时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厉声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主要信源:(新华网——“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洞见与忧思) 1966年盛夏的北京城,蝉鸣声嘶力竭地穿透东厂胡同的宁静。 梅汝璈书房里的旧电扇吱呀转动,却驱不散午后的闷热。 突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木门被猛地推开,一群身着绿军装的年轻人涌进小院。 为首的青年一把掀翻书柜,泛黄的法律文献散落一地。 "搜!把封资修的东西都找出来!" 带头者高喊着。 混乱中,一个瘦高个青年从壁橱深处拖出个樟木箱子。 箱盖开启时,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黑色法袍映入眼帘。 袍子袖口已磨出毛边,前襟留有淡淡的墨水渍。 "这破衣服还挺讲究。" 青年抖开法袍,作势要撕。 一直静坐藤椅上的梅汝璈突然起身,花白的眉毛剧烈颤动: "放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满室喧嚣戛然而止。 这件看似寻常的法袍,曾见证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历史性时刻。 1904年冬,江西南昌梅村的私塾里,小梅汝璈蜷在炭盆边偷看《国际法概论》。 窗外飘雪,书页上的拉丁文律条让他忘却严寒。 教书先生戒尺落下时,少年突然抬头问: "老师,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受洋人法律管?" 十二岁考入清华那日,他背着蓝布包袱站在校门前,望着罗马柱拱门暗暗发誓要研习最先进的法律知识。 1924年远渡重洋的邮轮上,这个清瘦青年始终立在甲板前沿,任海风鼓起长衫。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灯总在深夜为他独亮,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比较研究。 1946年春,东京帝国饭店套房里,梅汝璈轻轻抚平刚送来的法官袍。 真丝面料在灯下泛着幽光,他想起离京前老父的叮嘱: "此去关乎民族尊严。" 次日庭前,当书记官试图将中国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时,他当场取出受降书副本: "日本是在'密苏里'号上向中美英苏等九国投降,请按签字顺序排列。" 审判席上的日日夜夜,这件法袍见证了多少惊心动魄。 松井石根的律师狡辩"南京事件属于战争常态"时,梅汝璈的法官锤重重敲下,震得面前茶杯晃动。 出示百人斩战犯的军刀证据时,他特意让法警将战刀捧到被告席前,刀身上的血槽在灯光下异常清晰。 最激烈的量刑辩论阶段,他连续三夜未眠,将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名单逐一核对后附入判决意见书。 1948年深秋,巢鸭监狱的行刑室传来绞架声响时,梅汝璈正在住处小心熨烫这件陪他征战两年半的法袍。 蒸汽氤氲中,他想起南京法庭审判谷寿夫时,旁听席上遇难者家属的哭泣声。 1949年那个春雨绵绵的清晨,放在客厅茶几上的船票渐渐被雨水洇湿。 梅汝璈望着窗外新发的梧桐叶,对来客轻轻摇头: "我的法律知识应该留给新中国。" 他转身从衣橱取出那件法袍,在箱底铺上樟脑丸,动作轻柔得像在安置一位老友。 文革初期,当抄家者翻出这件象征"旧法统"的袍服时,七旬老人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他扑上前护住衣箱,嘶声喊道: "这是东京审判的见证!" 激动的青年们愣住了,他们看见老人浑浊的双眼迸发出锐利的光芒,那目光仿佛能穿透时光,直抵1946年的远东军事法庭。 晚年住在东厂胡同的那些年,梅汝璈常对着衣柜里的法袍出神。 有次孙女好奇想摸袍子上的金绣,被他轻声制止: "这上面沾着三十万亡魂的血泪。" 2003年,当这件见证历史的法袍被捐给国家博物馆时,保管员发现内衬有用丝线绣的细小日期"1946.5.3-1948.11.12"。 如今,博物馆展厅的灯光下,这件静止的法袍仍在无声述说。 磨损的袖口记录着梅汝璈在审判席上翻阅卷宗时的坚持,衣领的汗渍保留着那个时代中国法律人挺直的脊梁。 每当参观者驻足,似乎还能听见历史深处的法槌回响——那是一个民族用法律讨回公道的庄严时刻。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