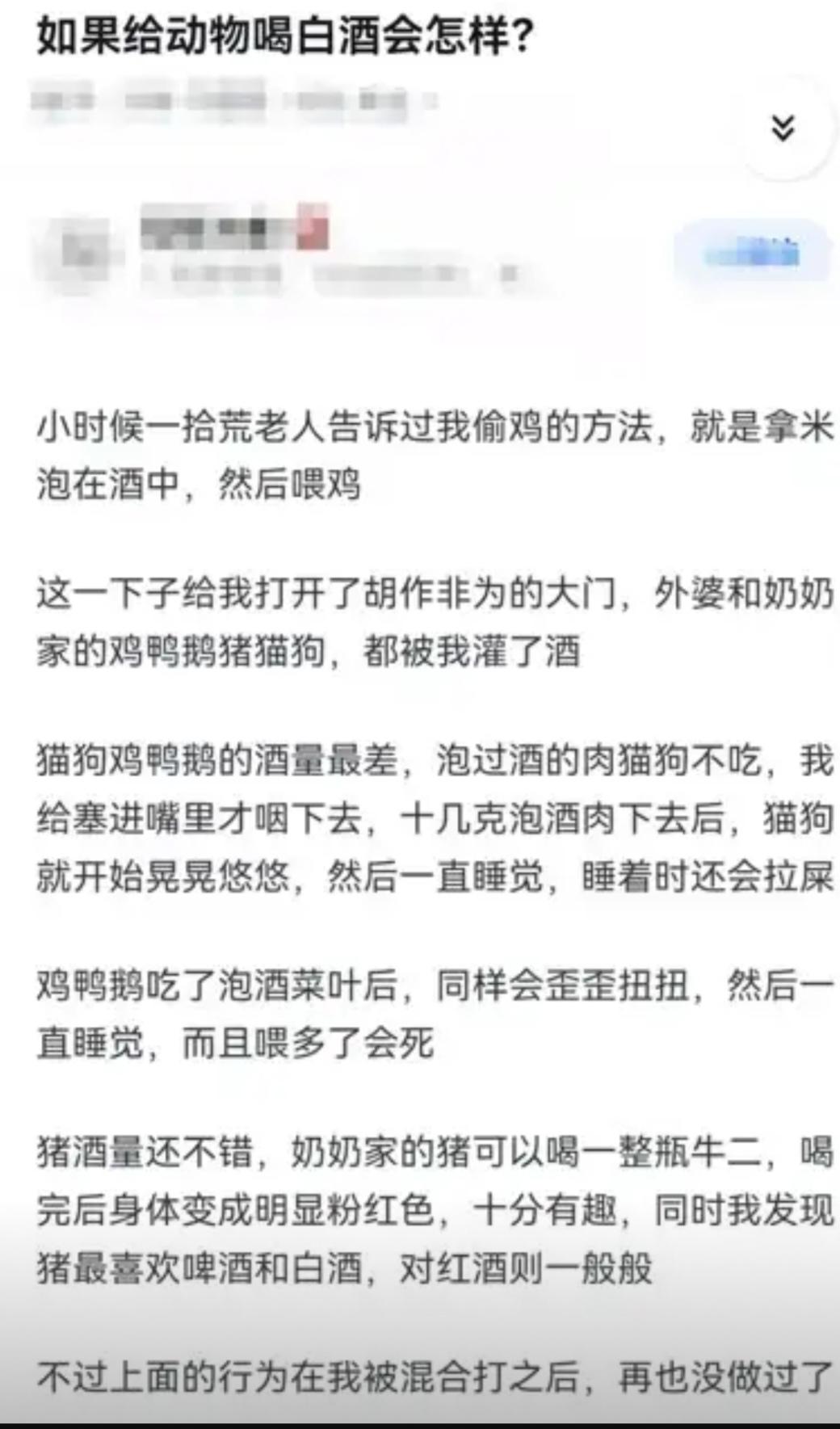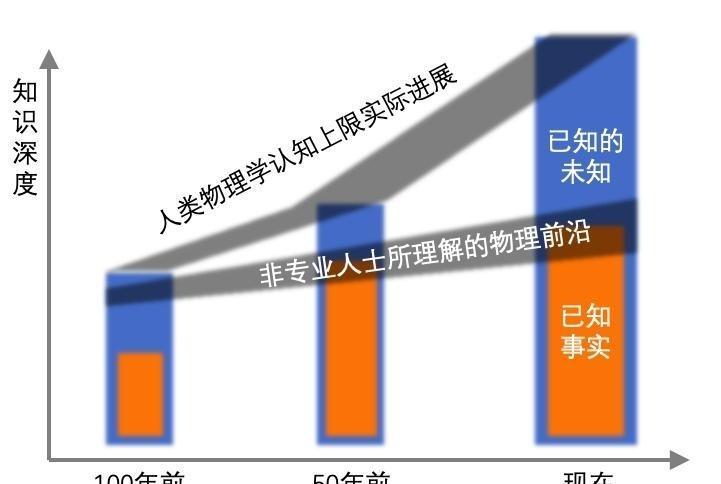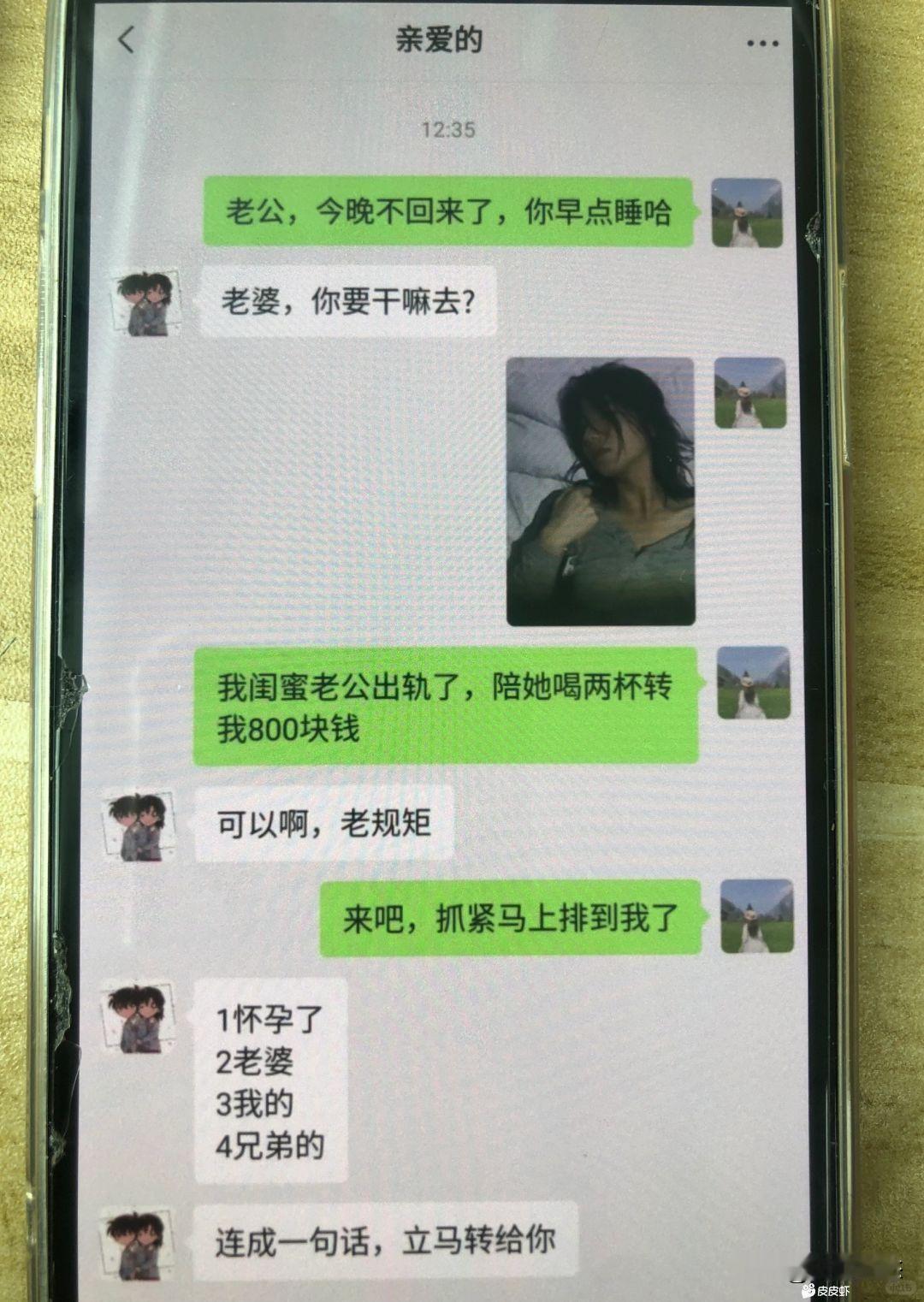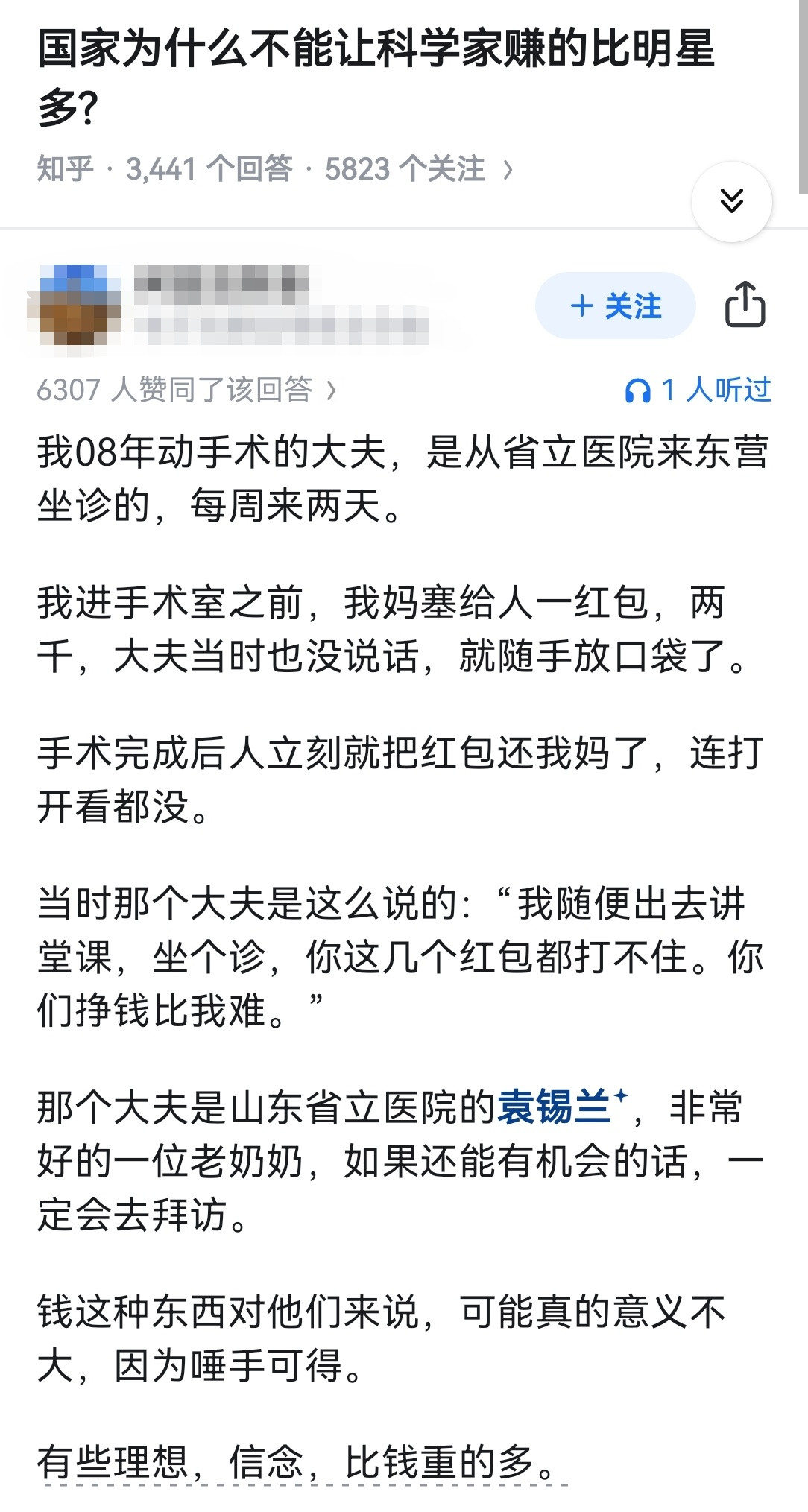1879年,俄国科学家在忙完一天的化学实验后,不洗手就准备吃饭了,结果他却发现,自己食用的牛排和沙拉里,竟然有种奇怪的甜味。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康斯坦丁·法利德别尔格1850年出生在俄国的一个小城市,父亲是药剂师,从小耳濡目染,他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漂洋过海,先在德国学了几年化学,又辗转到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验室,成为知名教授伊拉·雷姆森的助手,那时的化学家,对煤焦油着了迷,别看煤焦油黑糊糊、气味呛人,它却是19世纪化学研究的“藏宝箱”,染料、药物,甚至香精香料的原料都能从中提取。 法利德别尔格每天跟煤焦油打交道,分离、反应、分析,常常从早忙到晚,实验室里的玻璃器皿和各种溶液,他摸得滚瓜烂熟,有时候,研究做得入迷,连洗手这样的“小事”都顾不上,终于,机缘巧合降临在一次“糊涂”的夜晚。 那天傍晚,他刚结束实验,就急匆匆回家吃晚饭,刚动刀叉,嘴里突然蹿出奇怪的甜味,牛排、沙拉居然都像抹了糖一样甜,他疑惑地看了看妻子,妻子也满脸纳闷,说没放糖,他这才反应过来,也许是手上残留的化学物质带来的甜味,科学家的直觉让他立即回到实验室,仔细检查当天接触过的化合物,反复比对后,他终于确定,这种异常的甜味来自一个不起眼的副产物——邻苯甲酰磺酰亚胺钠,这个名字拗口的东西,后来被命名为糖精。 初步测试发现,糖精的甜度远远超过蔗糖,而且几乎不含热量,法利德别尔格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振奋,敏锐地意识到,这也许能在食品领域大有作为,他与导师雷姆森一同进行了大量实验,进一步研究糖精的性质和合成方法,随后,他们将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新型甜味剂。 不过,事情的发展很快超出了学术圈,法利德别尔格自己申请了糖精的生产专利,还在德国建了工厂,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糖精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进而进入市场,逐步出现在饮料、糖果、药品等各种产品中,它的高甜度和低成本,使其尤其受食品工业青睐,最初,糖精还主要用于特殊人群,比如糖尿病患者,他们终于可以放心享受甜食,而不用担心血糖升高,随着技术进步,糖精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从无糖饮料、口香糖到日常调味品,糖精逐渐成为现代食品工业不可或缺的角色。 历史进程中的糖精,也曾多次充当“救兵”的角色,比如一战期间,蔗糖因为战争而短缺,糖精成了战壕里的补给品,士兵和普通家庭一样,用糖精来满足对甜味的渴望,后来,二战中同样上演了类似的情景,糖精的低价和高甜度帮助了无数家庭和工厂度过物资紧张的时期,食品制造商发现,用少量糖精就能替代大量蔗糖,既省钱又高效。 当然,这种化学甜味剂也并非一帆风顺,从20世纪初,糖精就伴随着不断的争议,最早的争论是学术归属,雷姆森认为糖精的发现和合成离不开自己的指导,专利和商业利益却都被法利德别尔格拿走,两人最终反目,这场“师生内讧”成了科学史上的典型案例。 但更大的争议还在后头,随着糖精普及,关于其安全性的担忧不断浮现,1960年代,一些实验显示高剂量糖精可能导致大鼠膀胱癌,这一消息在媒体上炸开了锅,消费者人心惶惶,政府也不得不出面介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一度提出全面禁用糖精,但食品行业和大量消费者反对,国会最终妥协,只是在包装上要求添加健康警示,接下来几十年,科学界不断开展新研究,后来的数据表明,实验动物吃到的糖精剂量远超普通人类的摄入水平,实际风险没那么高,到1990年代,糖精逐步“洗白”,官方移除致癌标签,继续允许作为食品添加剂流通,尽管如此,国际上仍有分歧,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其列入“可能致癌物”,但证据并不充分,市场监管始终没有放松。 这期间,食品工业和科学界对甜味剂的探索从未停止,糖精之后,科学家们陆续开发出其他人工甜味剂,比如阿斯巴甜、三氯蔗糖,还有天然提取的甜菊糖苷、赤藓糖醇等,每种新甜味剂都自带光环和争议,优缺点各不相同,消费者一方面渴望低热量、低血糖的健康选择,另一方面又对化学合成产品保持警惕,正是在这种矛盾拉扯下,现代超市的货架才会有那么多花样繁多的甜味剂供人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