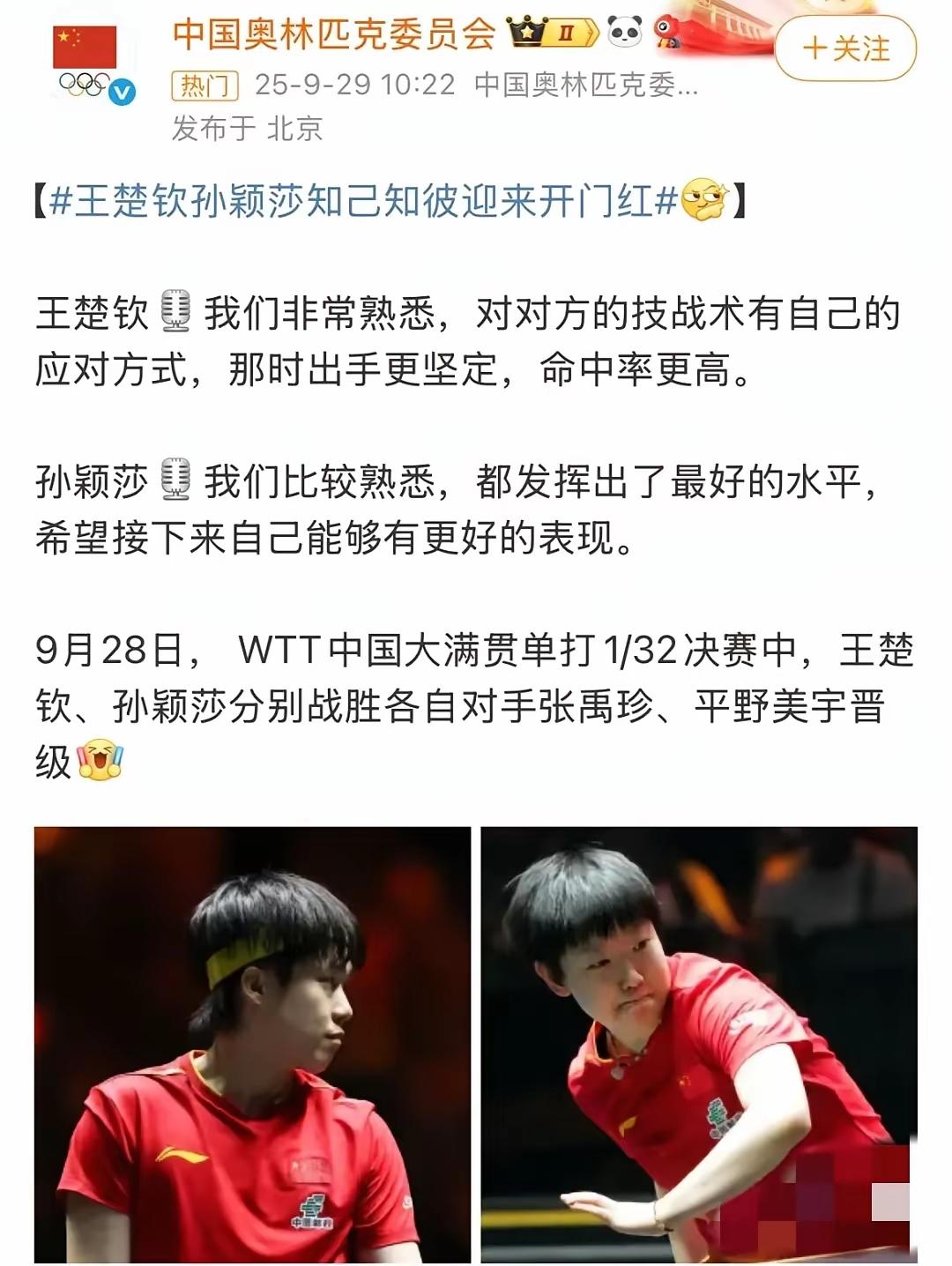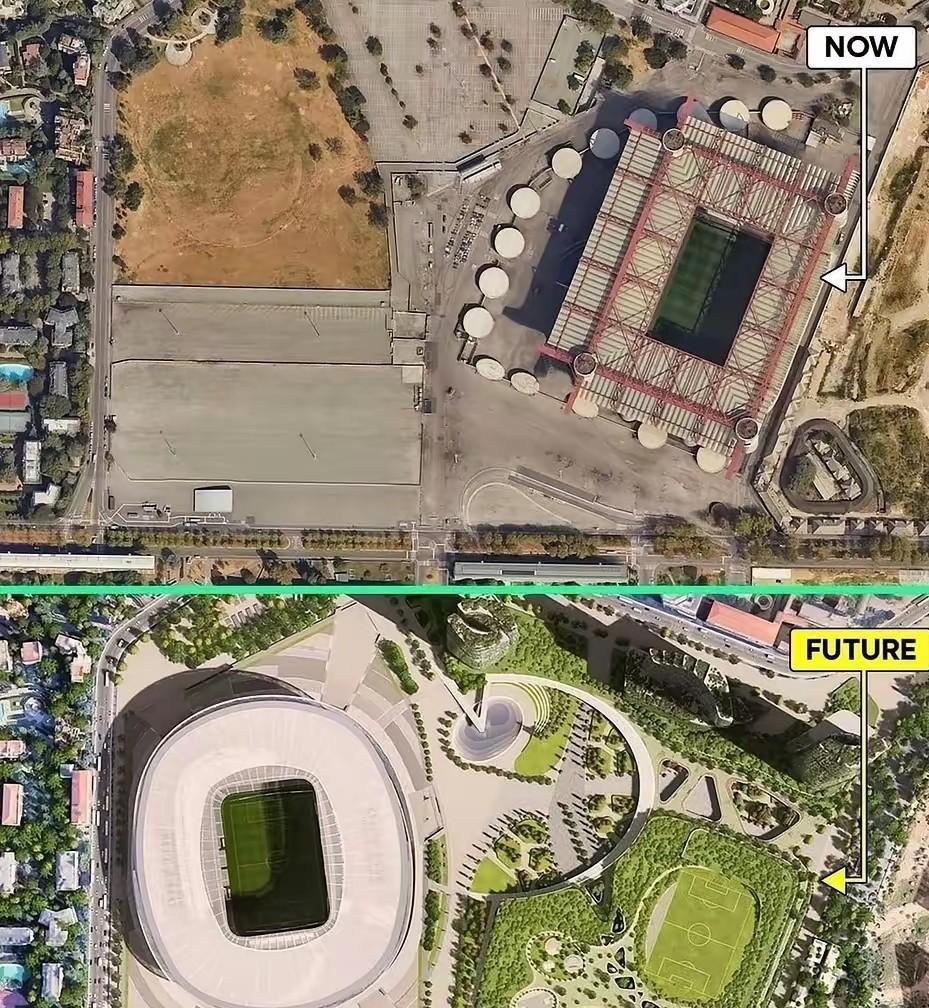[微风]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决定尝试一番。 1971 年,钱学森带回来两页纸,上面写着美国最先进的激光陀螺技术原理,当这两页薄薄的纸被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后,大家看了都没了声音,也没人敢接手研究。 要知道,没人敢接,不只是因为大家不熟悉这项技术,而是因为当时我们和美国的技术差距太大,美国早在 1960 年就做出了激光陀螺成品,还严格了封锁技术;而我们呢,连最基础的镀膜技术,精度都比人家差十倍,有人说,这简直是差了好几个时代。 就在大家都沉默的时候,一个 47 岁的老师站了出来,他叫高伯龙,高伯龙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平时研究的是理论物理和相对论,跟导航、光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他偏偏接下了这个没人敢碰的难题。 这就好比让一个大学老师从零开始造复杂的电子产品,难度特别大,1975 年,钱学森还亲自找高伯龙谈话告诉他这这项工程的难度,但高伯龙听了后并没有退缩。 相反对于他来说,他目前最要做的就是搞懂激光陀螺的理论,为了能弄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高伯龙没有去模仿美国那套已经成熟却被封锁的技术方案,而是把自己关起来。 用了一年半时间,从相对论的基础开始,一点点反向推导,最后终于得出了激光陀螺的整个数学模型。 1976 年,高伯龙写出了一本《环形激光讲义》,后来这本书被称作中国激光陀螺领域的 “圣经”,更厉害的是,他根据国内当时工艺水平不高的情况,想出了一条没人走过的技术路线 ——“四频差动方案”。 这样一来,不仅避开了西方的专利限制,还大大降低了对制造精度的高要求,后来证明,这条路线最适合当时的中国。 理论搞懂了,可实际研究起来更难,他们的实验室在哪呢?一个漏风的木板房,还有一个废弃的食堂,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 “乞丐作坊”。 没有研究设备,他们就自己做:稳定平台是用从火车站捡来的废弃大理石板搭的;真空腔是用照相机的胶片筒凑合用的;为了攻克镀膜的难题,他们还自己做了一台 “差动检测仪”。 那时候做研究的日子特别苦,简直能把人逼疯,高伯龙调试设备时,鼻尖要紧紧贴着显微镜,时间长了,鼻梁都磨破了。 他的同事金世龙教授花了好几年时间,用手一点点打磨光学镜面,饿了就煮点挂面吃,不加菜不放料,过得像一支在野外工作的队伍,外人看到他们这样,都觉得这群人有点 “魔怔” 了。 也正因如此,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他们就在这个 “乞丐作坊” 里,硬是研究出了对国家很重要的激光陀螺。 1984 年,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样机终于做出来了,可高兴的日子没几天,新的难题又来了,这次是大家对这项技术的质疑。 有人说:“美国人早在 1978 年就放弃你们这条技术路线了,人家都去研究光纤陀螺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接着做激光陀螺?” 这话听着伤人,却也有一定道理,别人都放弃的路我们还要走吗?高伯龙的回答很平静:“外国没有坚持的,不代表中国不能做。” 说完,他又回到了实验室,这一埋头研究又是十年。他就是想证明,自己选的这条路是对的。 1994 年,由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带领的专家组来验收这项成果,结果让所有人都很惊讶:这台激光陀螺的精度达到了 0.001°/ 小时,换算一下,就算用一百年,误差也不超过一秒,远远超过了预期。 那一刻,70 岁的高伯龙终于能挺直腰杆了。中国,也成了全球第四个能独立掌握激光陀螺技术的国家。 那些曾经的质疑在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面前,再也没人提了,这台曾经被人觉得 “过时” 的激光陀螺,后来被装到了导弹、舰艇和无人机上。 有一款导弹装了这种激光陀螺后,打出了海军史上第一个 “百发百中” 的成绩;辽宁舰上,32 个激光陀螺组成的系统,能感知到甲板万分之一度的微小晃动,为舰载机起降提供保障。 中国,也成了全球唯一能把这种平面结构的四频激光陀螺成功用在武器上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做的激光陀螺,成本只有进口的十分之一,而且从研发到制造的全流程,都能自己把控,不用依赖外国,高伯龙当年的坚持为国家换来了重要的战略价值。 2017 年,高伯龙去世了,去世时手里还紧紧攥着最新的激光陀螺设计图,嘴里最后念叨的一句话是:“膜层系数要再调 0.05”。 就在他离世那天,搭载着他研究的激光陀螺技术的北斗卫星正从中国的上空飞过,高伯龙用一辈子证明了,真正的技术突破不取决于条件好不好,而在于你有没有勇气选择,有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念。 信息来源:新华网--永不停转的“陀螺”——追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