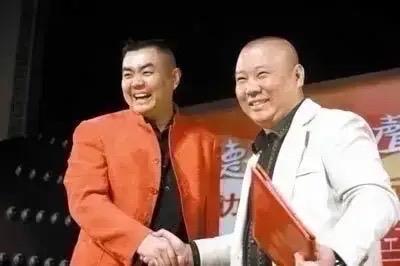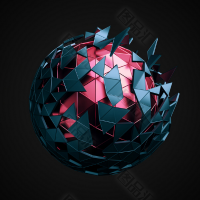有一次,主持人问李菁:“你离开德云社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李菁说了2点,却让郭德纲的粉丝们哑口无言。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北京的冬天总是来得特别早,1995年的德云社还在襁褓之中。
那时的广德楼剧场里,观众席常常空着一大半。
李菁裹着厚厚的棉衣,在后台一遍遍地擦拭着他的快板。
这个从小就被称作"神童"的年轻人,此刻正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
七岁那年,李菁就能把《珍珠翡翠白玉汤》背得滚瓜烂熟。
母亲用老式录音机录下他稚嫩的童声,那盘磁带至今还珍藏在家中的抽屉里。
如今站在空旷的剧场里,他依然记得第一次登台时手心的汗水。
台下只有二十来个观众,但他照样说得起劲,仿佛面对的是满堂彩。
与此同时,在城南的花市上,何云伟正为他的花摊发愁。
这个刚从园艺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总学不会做生意的那套。
一束成本60元的花,别人讨价还价,他就真的60元卖出,连摊位费都赔了进去。
直到某天,他偶然走进广德楼,听见台上有板有眼的相声,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舞台不该在花市。
德云社的早期岁月充满艰辛。
郭德纲常常带着几个徒弟,在天桥底下卖艺。
李菁记得最清楚的是1998年那个雨夜,演出结束后,大家凑钱只够买一袋包子充饥。
但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何云伟还是坚持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练功,把传统段子反复打磨。
转机出现在新世纪。
随着电视媒体的传播,德云社突然火了起来。
剧场外开始排起长队,演出票一票难求。
但热闹背后,裂痕也在悄悄产生。
李菁发现,新来的学员才练了三个月就要上台,传统的"说学逗唱"基本功被压缩成了速成班。
2008年春天,一场普通的排练后,李菁和何云伟在后台长谈。
何云伟拿出父亲留下的怀表,那是他学艺时师父送的礼物。
"现在的段子越来越短,包袱越来越密,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李菁望着窗外车水马龙,想起师父说过,相声是手艺,得慢慢熬。
真正让两人下定决心的是2010年夏天。
那天演出结束后,新来的学员围着郭德纲讨论商演报价,而李菁还在后台纠正徒弟的发音。
他耐心示范着,但徒弟的眼睛一直瞟向隔壁热闹的讨论圈。
何云伟站在幕布后,轻轻叹了口气。
后来有记者采访李菁时问道:"你离开德云社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李菁的回答很实在,艺术理念不合,做事方式不同。
他说自己从小学习相声,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可现在一切都太快了,快得让人喘不过气。
这话一出,连郭德纲的铁杆粉丝也无话可说。
离开的过程并不激烈,更像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告别。
他们最后一场德云社的演出,选的是传统段子《夸住宅》。
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没人察觉这是告别演出。
谢幕时,李菁特意摸了摸用了十多年的醒木,何云伟则把大褂叠得整整齐齐。
"星夜相声会馆"开张那天,来了不少老观众。
李菁重新挂起手绣的桌围,何云伟坚持用传统的报幕方式。
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票友特意从天津赶来,说:"这才是老味儿。"
如今,李菁偶尔还会路过德云社旧址。
那里已经变成繁华的商业区,但他总记得1996年冬天,第一次和郭德纲、张文顺在这里说相声的场景。
三个年轻人围着小煤炉,呵着白气对词,梦想着相声的明天。
何云伟的书房里,至今挂着当年广德楼的老照片。
有时夜深人静,他会泡一壶茶,对着照片轻轻念叨几句《八扇屏》。
窗外的北京城灯火通明,而在他心里,永远留着那个简单纯粹的相声梦。
这些年,李菁和何云伟的星夜相声会馆办得有声有色。
他们不仅在国内演出,还把相声带到了海外。
在伦敦的剧场里,外国观众虽然听不懂全部内容,但也会被他们的表演逗得开怀大笑。
这种跨文化的交流,让他们看到了传统艺术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