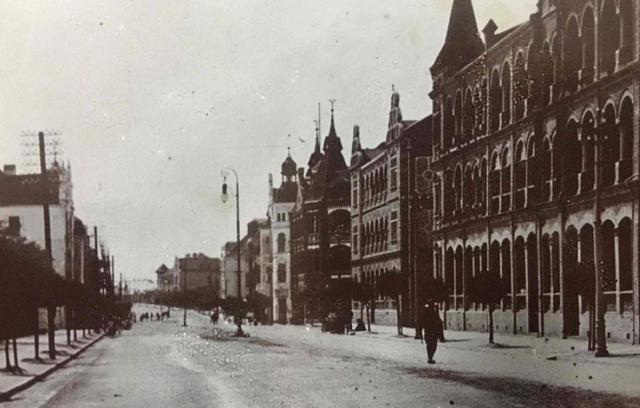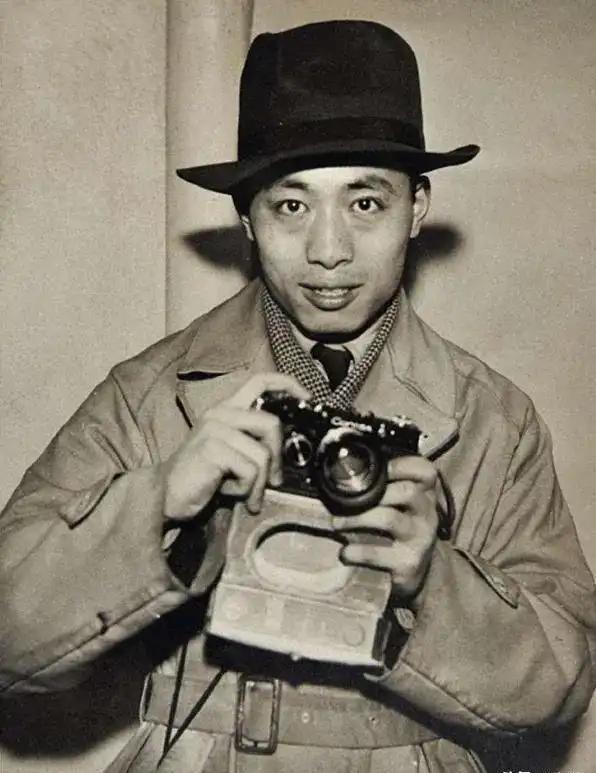1945年,盟军以破竹之势攻入德国,开启了德国女性的噩梦。不久后,盟军撤兵,德国女性又坠入另一个深渊! 1945年的春天,德国的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和绝望的味道。当盟军的坦克碾过柏林的街道时,对于纳粹德国来说,是末日;但对于德国女性,噩梦才刚刚拉开序幕。 我们听过太多关于苏联红军在东部德国的复仇故事。确实,被纳粹铁蹄蹂躏了四年的苏联人,把满腔的仇恨都倾泻在了这片土地上。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在他的《柏林:1945年的沦陷》里,描绘了地狱般的场景,据估计,仅在柏林,就有超过10万名女性被强暴。数字是冰冷的,但背后是无数个破碎的家庭和被撕裂的人生。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只盯在苏联人身上,那就掉进了西方世界在冷战时期精心编织的叙事陷阱里。事实上,暴行,是所有“胜利者”不受约束的权力狂欢。 德国历史学家米里亚姆格布哈特花了数年时间,翻遍了德国、美国等国的档案,写成了一本名为《当士兵们到来时》的书。她得出了一个让西方世界非常尴尬的结论:在德国西部,美军、法军、英军同样犯下了大规模的性暴力罪行。 据她统计,至少有19万德国女性被美军士兵强暴。法国军队,特别是其麾下的摩洛哥部队,在斯图加特等地的暴行,更是令人发指。一个叫玛尔塔的德国女人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俄国人。明天,可能是美国人。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只是被征服的女人。” 在战争的逻辑里,女人的身体,往往被当作战利品,一种最原始、最直接的征服象征。她们的遭遇,成了那段历史中最不堪、最被急于遗忘的一页。对这些德国女性来说,1945年的春天,没有解放,只有不同制服下的同一场噩梦。 枪声总会停息,军队也总会换防或撤离。当最初的混乱和暴力浪潮退去,德国女性以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们错了。一个更漫长、更磨人的深渊,正在等着她们。 这个深渊,来自她们的同胞,她们的家人,来自这个刚刚从废墟里站起来,却急于抹去所有耻辱印记的社会。 首先是那“巨大的沉默”。 整个德国社会,对这场波及数百万女性的灾难,选择了集体失声。男人们从战场或战俘营回来,他们看到的是断壁残垣的家,和眼神躲闪的妻子。他们不想听,女人们也不敢说。说出来,换来的不是安慰,而是“不干净”、“耻辱”的标签。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极端保守的社会里,受害者,反而成了罪人。 很多幸存的女性,带着这种创伤和秘密,活了一辈子。直到临终前,才向自己的儿女,或者神父,吐露出那个压抑了一生的夜晚。 如果说沉默的创伤是内心的深渊,那么那些“占领军儿童”的存在,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深渊。 据最新的学术研究估计,战后德国出生的“占领军儿童”超过40万。这些孩子的父亲,是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他们的母亲,独自一人,在一个视他们为“敌人的孩子”的国度里,艰难地将他们抚养成人。 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处境,在学校里,他们被叫做“美国杂种”或者“俄国猪”。如果父亲是个黑人,那情况就更糟了,他们会被叫做“巧克力娃娃”,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什么昵称,而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他们没有父亲,身份认同是混乱的。他们的母亲,则要顶着“军妓”、“叛国者”的骂名,在贫困和白眼中挣扎。 这就是第二个深渊。它不像枪炮那样轰轰烈烈,却像水蛭一样,附着在两代人的生命里,吸食着他们的尊严和安宁。它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战争最深远的伤害,往往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在人心最幽暗的角落。 如今,80年过去了。德国早已从废墟中崛起,成为了欧洲的经济引擎。当年那些经历过噩梦的女性,大多已经离世。那些“敌人的孩子”,也已步入暮年。 但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重提这段往事?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战争中每一个个体的痛苦,尤其是那些最无声的受害者的痛苦,那我们对战争的反思,就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虚伪的。 历史不该只有英雄和战犯,还应该有那些被碾碎的普通人。她们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战争的旗号多么正义,一旦人性的枷锁被打开,地狱就会降临人间。而首当其冲的,永远是手无寸铁的女人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