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家胡也清说:“前有鲁迅,后有莫言!二者均以文学为镜,照见民族的症结!” 鲁迅的作品如一把手术刀,直击近代中国的病灶。《阿 Q 正传》中,阿 Q 的 “精神胜利法” 堪称民族劣根性的经典缩影 —— 面对压迫不敢反抗,却以自欺欺人的方式寻求心理慰藉,这正是当时部分国民麻木、懦弱心态的真实写照。《药》里,华老栓为救儿子买人血馒头,围观群众对革命者夏瑜的牺牲冷漠旁观,深刻揭露了封建思想对民众的精神禁锢,以及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的愚昧与麻木。鲁迅用冷峻的文字,撕开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背后的精神疮疤,让读者在刺痛中直面民族的症结。 莫言则继承了这种文学担当,以魔幻与现实交织的笔法,照见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复杂问题。《丰乳肥臀》中,上官家族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既展现了母性的伟大,也折射出特殊历史时期里,个体在集体意志下的渺小与无奈 —— 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忍受饥饿、战乱与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其中暗含对民族在苦难中盲目跟随、丧失个体思考的反思。 无论是鲁迅笔下近代中国的愚昧与麻木,还是莫言书写的当代社会的苦难与矛盾,二者都没有回避民族发展中的痛点。他们以文学为镜,不美化、不掩饰,让读者在阅读中看清民族的症结所在。 回想一个多世纪前,鲁迅在日本求学时,一场特殊的 “观影” 经历,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敲醒了他。那是在课堂上,日本老师播放的时事幻灯片,画面中,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肆虐,日军抓捕了一名被指为俄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即将行刑。而周围围观的,竟是一群面无表情、麻木不仁的中国同胞。他们眼睁睁看着同胞被处决,眼神中没有愤怒,没有悲痛,只有冷漠与麻木。这一幕,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心,也让他深刻意识到,国人的 “病”,不在身体,而在灵魂。那些冷漠的看客,仿佛被无形的绳索束缚,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情感和思考能力,沦为了 “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自那之后,“看客” 便成为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形象,他以笔为刀,对这种麻木、冷漠的 “看客” 心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药》里,革命者夏瑜为了理想而牺牲,可那些围观的民众,却把他的鲜血当成治痨病的 “药引”,在他们眼中,夏瑜的死不是一场悲剧,而是一场可以满足他们猎奇心理的闹剧。《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的酒客们,以取笑落魄的孔乙己为乐,孔乙己的痛苦与窘迫,成了他们生活中的调味品。还有《祝福》里,鲁镇的人们对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先是好奇地围观,然后是麻木地无视,最终将她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鲁迅对 “看客” 的批判,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成为其作品中最具震撼力的主题之一。他通过这些生动的描写,揭示了当时社会集体意识的麻木,人们缺乏对他人的共情和对现实的思考,只是盲目地随大流去围观、议论,却看不到社会的问题和自身的处境。鲁迅的呐喊,如同一束强光,试图穿透那层厚厚的麻木之幕,唤醒沉睡的国人 ,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愚昧与冷漠,从而寻求改变,走向觉醒。 时光流转,一个世纪后,莫言带着他的《檀香刑》横空出世,这部作品宛如一座桥梁,横跨在鲁迅的文学世界与当代文学之间,承接了鲁迅对 “看客” 主题的深刻洞察,并以独特的方式将其延续和拓展 。 《檀香刑》以晚清为时代背景,彼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西方列强的侵略与腐朽的封建统治,让这片土地陷入了深深的苦难。莫言将目光聚焦在一场残酷的刑罚 —— 檀香刑上,以此为切入点,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又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画卷。 在小说中,檀香刑的行刑场面堪称震撼。那是一个阳光刺眼的日子,刑场周围早已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如同潮水般涌来,将刑场围得水泄不通。这些看客们,身份各异,有衣衫褴褛的贫苦百姓,有身着长衫的文人墨客,还有耀武扬威的达官贵人。他们怀揣着不同的目的,却都有着同样炽热的好奇心,仿佛即将上演的不是一场残酷的刑罚,而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大戏。 当受刑者孙丙被押上刑场的那一刻,看客们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过去,眼神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那是一种夹杂着兴奋、好奇与冷漠的复杂神情。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对孙丙的悲惨遭遇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像是在讨论一件与自己毫无关联的趣事。有人在猜测檀香刑的具体过程,言语中充满了猎奇的渴望;有人则在嘲笑孙丙的 “愚蠢”,仿佛自己站在了道德与智慧的制高点。他们的脸上,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没有对正义的追寻,只有麻木与冷漠。 这与鲁迅笔下的 “看客” 何其相似!同样是面对他人的痛苦与不幸,同样是冷漠地围观,将他人的悲剧当作消遣的谈资。他们的灵魂,被封建礼教的阴霾所笼罩,被愚昧与无知所蒙蔽,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良知与情感。在他们眼中,他人的生命如同蝼蚁一般,微不足道,而自己,只是这场残酷戏剧的旁观者,只需尽情享受其中的刺激与新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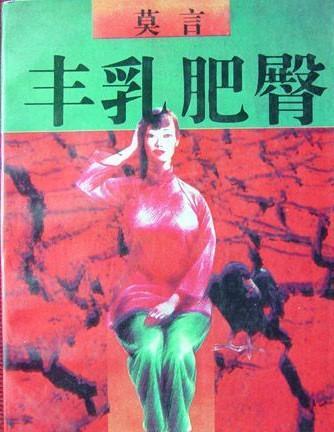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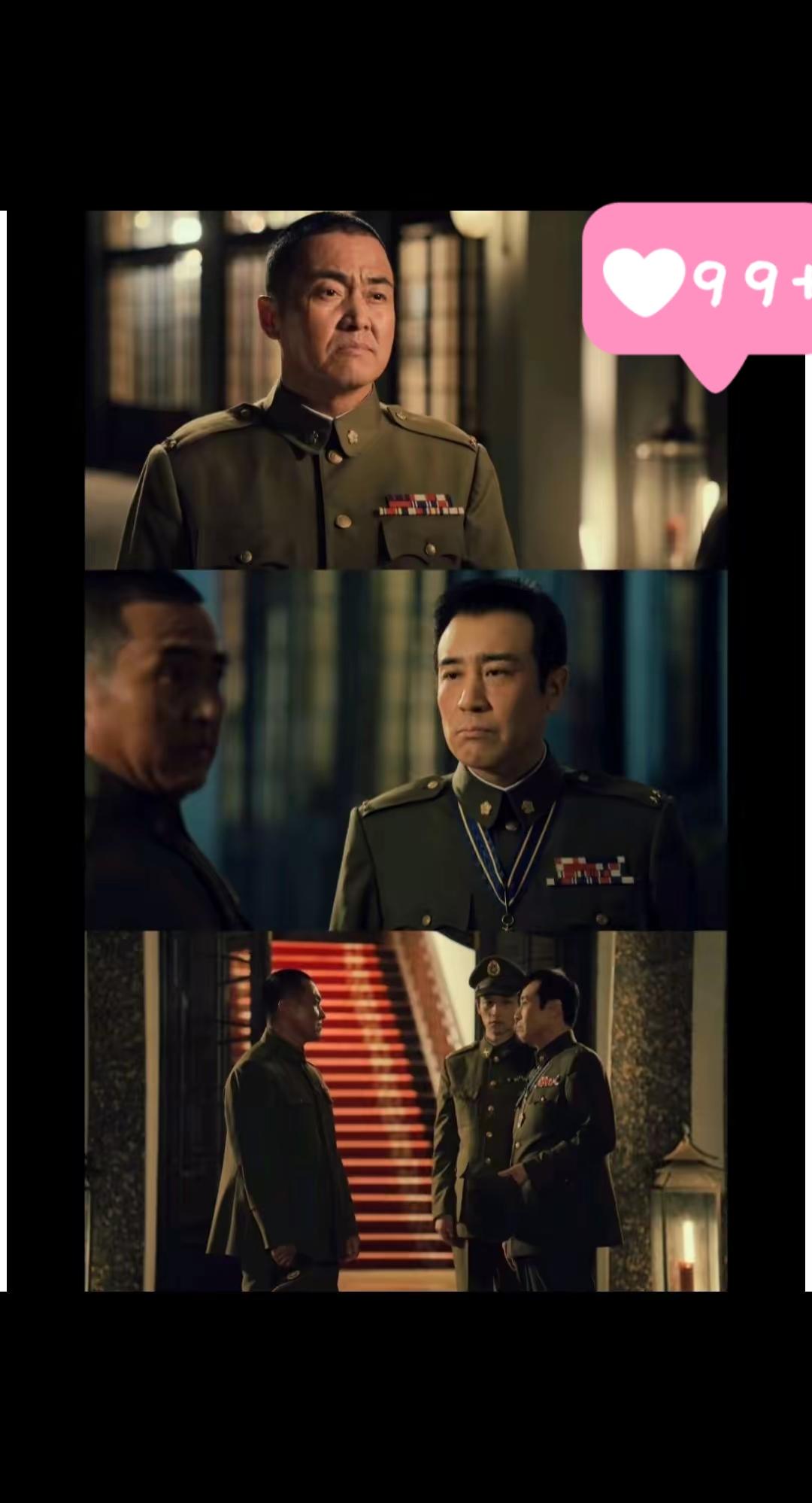
![朱一龙檀健次空枪非官宣不约,一切尊重檀健次个人选择[作揖]](http://image.uczzd.cn/4106048299465773991.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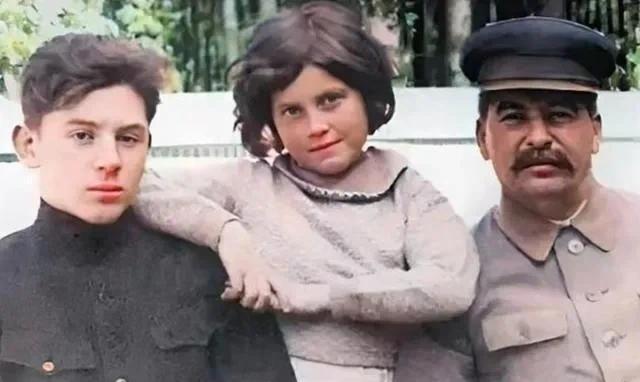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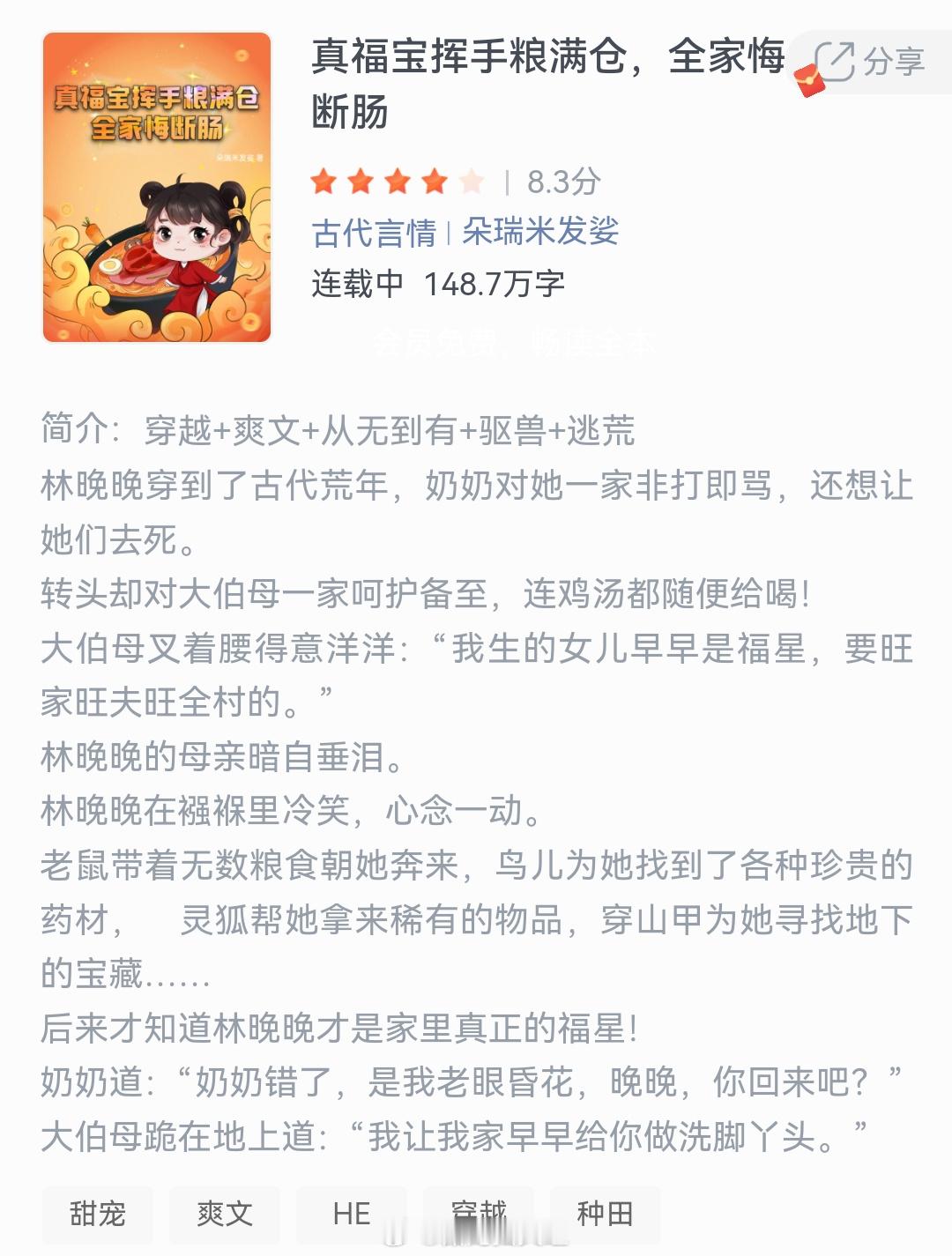


用户17xxx01
别扯了,鲁迅的文字哪有那么骚
深山老林 回复 09-17 11:14
是一个时代么?鲁迅盼望着中国有一天能强大。莫言盼望着中国哪一天回到八国联军那个时候认祖归宗。
大牛
投敌所好写手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