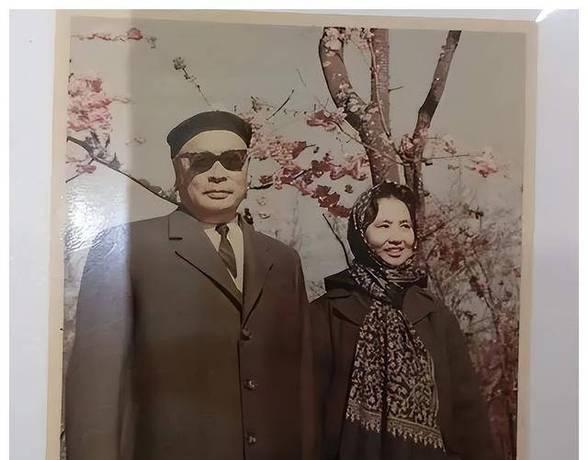1935年的冬天,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1935年的冬天,贵州遵义的气氛冷得像冰。红军的处境比天气还糟,湘江边上的一场惨败,让八万多人的队伍锐减到不足三万,而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正像一张大网,越收越紧。生死存亡,就悬在这口气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一场足以决定未来命运的会议悄然召开。当有人提议,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毛泽东时,会议室里响起了反对的声音。 反对声中,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直接的,正是来自凯丰。他不是跟谁有仇,而是打心底里觉得,这么大的变动太仓促,怕部队乱了阵脚。在他看来,坚持既有的路线才是稳妥之举,这是一种源于思想惯性的担忧。 另一个反对者,是当时的总负责人博古。而他表现出的态度,就显得微妙不少。会议一开始,他就主动承认指挥上有失误,愿意背这个锅。可当听到要他交出指挥权时,他却迟疑了,只说:“要再考虑考虑。”” 这句“考虑”,背后藏着复杂的情绪。既有作为最高领导对这份天大责任的审慎,也难免有权力即将旁落时的迟疑。一个担心路线跑偏,一个掂量权责得失,这两种反对,构成了当时转向的最大阻力。 面对这种僵局,毛泽东没有回避。他直接接过博古的话:“赞成考虑,但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交出职务,而不是要不要交。” 这话一下就点到了要害,把议题从“是否要变”强行拉到了“如何去变”的轨道上,堵住了拖延的口子。 整个会议的气氛,紧张但实在。这不是一场剑拔弩张的权力斗争,更像是一次允许所有人讲真话的内部诊疗会。 周恩来坦率地承担了自己的军事责任,张闻天也尖锐地批评领导层脱离实际。大家心里都清楚,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党和红军活下去。 最终,那些存在的分歧,在直面问题、坦诚交流的讨论中渐渐被熔化。会议作出重要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构成的“三人团”。 此“三人团”被赋予全权,将全面承担军事指挥之重任,引领军事行动有序开展。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人事变动,它标志着生搬硬套苏联模式的指挥方式走到了尽头,“实事求是”的种子,在这一刻真正破土而出。 战略的转变立竿见影。新的指挥核心不再死守硬拼,而是变得异常灵活机动。紧接着的四渡赤水和巧渡乌江,就像一部精彩的悬疑片,让濒临绝境的红军硬生生撕开了包围圈,重新掌握了主动。 无需过多言说,历史本身便已为这一切,留下了最具分量、最有力的注脚。博古和凯丰在会后并没有被边缘化,依旧留在中央工作。 这证明了遵义会议的焦点始终是路线的正确与否,而非个人恩怨。它像一座熔炉,淬炼掉了错误的思想,却保全了同志间的团结,为这支队伍找到了唯一正确的航向。 信源:遵义会议最瞧不起毛泽东的中央委员是谁?2014-10-01 15:10·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