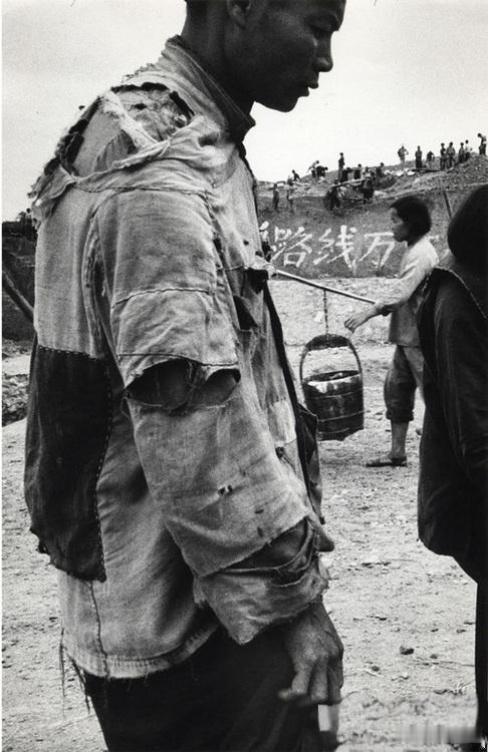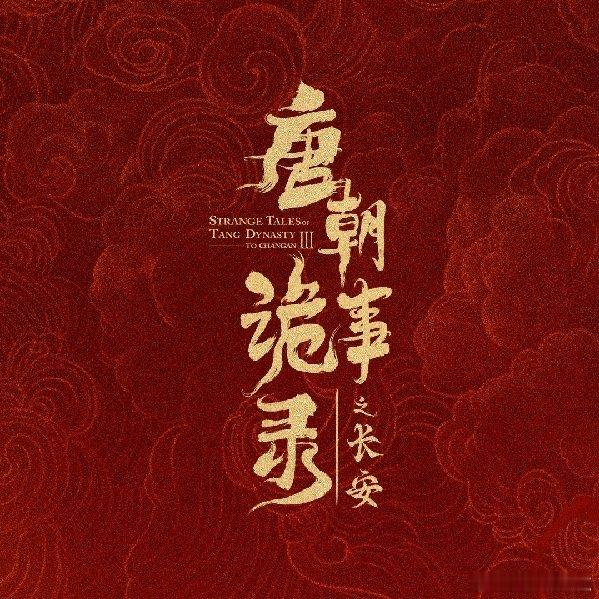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除了元帅,还有哪些开国将领也擅长 “1948年11月12日凌晨一点,报告司令员,敌军第三师向碾庄集结!”“让他们来,一并解决!”短短两句对话,在前线指挥部的煤油灯下显得格外干脆。那晚发号施令的人并非元帅,却要调度数十万兵力,他的名字叫粟裕。 既然开场已落在淮海战场,就先谈谈“规模”这个概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共中央直接掌握的正规部队只有八路军、新四军,总人数不足十万,连一个整编集团军都凑不齐。彼时的战斗,多是团旅级“麻雀战”,灵活,却谈不上大兵团运用。八年抗战耗尽侵华日军锐气,也给八路军赢得壮大空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解放区武装已逾百万,为日后成规模拼杀打下人力基础。 国共两党在1946年全面摊牌后,战场规格瞬间升级。蒋介石动员了350万军队,坦克、野炮一应俱全。红军出身的指挥员若不迅速掌握“集团军打法”,结局大概率会是被围堵、被分割。也正因为此,解放军内部对谁能指挥几十万人的“大会战”高度敏感——不仅关系胜负,更关系士气与未来政权。 四野的林彪、东北的一代元帅,确实以闪电般的“十二天结束锦州”名震天下;二野的刘伯承徐向前在中原一路奇袭,同样经典。然而,人们往往忽略另一条战线:华东。一野在西北打机动,二野、四野已具“兵团式”雏形时,华东野战军还夹在鲁南平原与江淮水网之间,环境复杂、敌军精悍。粟裕升任副司令员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破传统旅团建制,拉起纵队,增加炮兵、通信、后勤,硬是把地方化部队捏成能打大会战的整体。 1948年9月济南战役,粟裕手里兵力约17万,对手王耀武近10万,双方第一次在华东展开“正面硬杠”。济南城墙高厚,守军火力足,一般指挥员多半会选择围而不攻。粟裕却下令夜袭机场,断空中支援;再集中重炮四小时轰击,城破于第三天。济南之役,以少胜多,但更重要的是:全程多兵种协同,火力集中度前所未有。华东将士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团以上成建制协同”的震撼。 济南之后不久,淮海战役大幕拉开。问题随之而来:130万人的调度、补给、情报,一旦失误,就会酿成灾难。中央军委原拟由刘伯承坐镇,但华东情况熟,最终还是交给粟裕。战役伊始,他坚持“先打黄百韬、再吃邱清泉”,节奏异常果断。参与会战的老兵回忆,当时粟裕批示只有一句:“敌能合而为十万,必先分而为两万。”朴素,却道尽大兵团分割包围的精髓。 值得一提的是,粟裕的“大会战思维”并非天赋一蹴而就,他在苏中、鲁南连打七仗,总结出“围点打援”“分批歼灭”的程式;随后又在孟良崮用近七万兵力吞掉张灵甫整编七十四师。一次次局部试验,让他敢于在淮海把“小灶”变“大锅饭”。从11月6日到翌年1月10日,淮海三阶段战役歼敌55万,解决了华东、中原乃至长江天险以北的国民党主力。若无这样的成绩,渡江作战也不可能风卷残云。 1949年春,第三野战军正式挂牌,兵力70万,下辖四个兵团。南京、上海一线纵深狭长、密布河网,既要快,又需保护国际城市。粟裕为避免“巷战消耗”,采用“正面牵制、侧翼切割”,让三野部队从镇江、无锡连破国民党外围据点,再南渡黄浦江,直逼市区,上海守军几乎没来得及组织顽抗。短短42天,蒋介石防线土崩瓦解。兵贵神速,粟裕在此役再次证明了自己不仅能打穿河之战,还能指挥城市、海港兼备的大纵深作战。 如果说粟裕是在国内战场完成“大兵团指挥”毕业论文,那么邓华则把“论文”拿到朝鲜战场做答辩。1950年10月,志愿军第一次入朝时总兵力13个军不足20万,分两纵队穿插。1951年初第五次战役前夕,兵力增至三个兵团近60万。彭德怀飞赴北京请示扩大战略目标时,明确表示“邓华可以独当一面”。在第二、五次战役中,邓华负责中线,指挥二十军、二十七军等部队,在三八线地区与联合国军反复拉锯。最大一次会战,他手中的部队超过17万人,炮兵、坦克、防空火力成规模配属。虽然最终没能一举推进到汉城以南,但稳固了中线,使志愿军赢得休整时间。不能否认,朝鲜半岛地形狭长,多山多水,指挥难度不亚于淮海平原,而邓华硬是在“钢铁火海”里保住了战线。 除粟裕、邓华外,也有人提到陈赓、韩先楚等人。这些将领在特定时期、特定战役亦承担过兵团级任务,例如陈赓在太原前线调度八万部队合围阎锡山,韩先楚在渡江后率第十二兵团九万余人抢占福建沿海。然而,他们受限于战区、时间段,未能在数十万级别的会战中反复锤炼,因此在“大兵团指挥”榜单里常被排在后列。 综合各战线表现可见:善于指挥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军队,并非仅元帅专利。粟裕通过华东战场三次“升级打怪”,将多兵种合成、后勤体系、信息传递打通;邓华在国外战场对付现代化敌军,完成跨国交通线和山地协同的挑战。两位将领未列元帅,却做到了元帅级别的“调度、统驭、取胜”,这份能力与贡献毋庸置疑,也是新中国军衔评定时授予“开国大将”与“上将”的深层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