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64岁高龄的左宗棠打到新疆敌占区时,突然有100多个衣着破烂的清朝官兵,激动的朝他奔来,等左宗棠看清楚后,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天山北麓,六十四岁的湘军统帅左宗棠,端坐于战马之上,扫视着前方被阿古柏叛军占据的广袤疆域。 西征大军旌旗猎猎,铁甲森森,正准备收复失地。 就在此时,前方戈壁滩,突然涌现出一群黑点。 斥候飞马来报,称似有百余名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者正朝大军奔来。 左宗棠眉头紧锁,怕是敌军来犯,命亲兵戒备。 然而,当那群人踉跄着奔至近前,看清他们身上那早已褪色、布满破洞却依稀可辨的清朝兵勇号衣时,左宗棠突然一愣。 领头的老兵,膝盖一软,跪倒在砂石地上。 他颤抖着抬起头:“大人!我们是景廉将军的兵啊!我们没死!” 这声呼喊,让左宗棠身躯剧震,滚鞍下马。 他踉跄上前,看到了老兵肩上那块被硝烟熏得焦黑、几乎难以辨认的营旗残片,“定边”。 三年前,伊犁陷落,景廉所部被围,朝廷久候无援,最终以“全军覆没”奏报。 谁能想到,在这天山脚下的绝域,竟还有这样一群被遗忘的孤魂顽强地活着! 左宗棠这位以铁腕著称的统帅,此刻竟老泪纵横。 左宗棠强抑心中翻江倒海的悲怆,扶起跪地的老兵。 “你们,如何活下来的?” 老兵指向身后一个同样瘦骨嶙峋的年轻人:“靠信!王二柱他爹咽气前说,朝廷不会忘了咱,大军早晚会来!我们就信这话!” 原来,在伊犁失陷后,残部退入雪山峡谷,与主力失联。 朝廷的补给早已断绝,他们如同被遗弃的孤儿。 为了活下去,只能开始寻找任何能吃的食物。 挖野菜,剥树皮,在雪地里凿冰取水。 白天,他们藏匿在山洞岩缝,躲避叛军的搜捕。 夜晚,则伺机袭击小股叛军,抢夺那点可怜的粮草和武器。 严寒、饥饿、疾病,如同无形的刽子手,日夜收割着生命。 两百多名同袍,最终,仅剩下眼前这百余名形销骨立的汉子。 这时,一个瘸腿的小兵挣扎着挤上前来,双手高高捧起半截残破的枪杆。 枪身布满凹痕,木质部分早已磨损不堪,但枪托上,“守土”二字,却清晰可见。 小兵哽咽道:“大人您看!这是我哥的枪!他死的时候说,枪在,新疆就还在咱们手里!” 左宗棠环视着这群衣衫褴褛、伤痕累累却目光如炬的士兵,胸中激荡着前所未有的悲愤与敬重。 他猛地转身,对身后的亲兵厉声喝道:“拿干粮!拿棉衣!取我的药箱来!” 他亲手将馒头塞进老兵的手中,随后当众宣布:“从今日起,你们皆入我亲兵营!跟着我,把被夺走的土地,一寸寸,夺回来!” 夕阳西下,百余名残兵捧着久违的热食,狼吞虎咽。 这样的场景,不禁让许多年轻的湘军士兵忍不住红了眼眶。 然而,人群中传来了异样的议论,”这些败军之卒为什么能受此优待?“ 左宗棠闻声,勃然大怒。 “败兵?何为败兵?他们被围困,粮尽援绝,却宁啃树皮,不降叛贼!宁冻饿而死,不弃守土之责!三年!他们用命守着这片疆土,此非败兵,此乃铁骨!我等粮饷、暖衣都不缺,有何颜面轻视此等以血肉守国门的弟兄?!” 质疑之声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无言的震撼与肃然起敬。 这百余名老兵,迅速成为西征军中最锋利的尖刀。 在随后攻打叛军重镇玛纳斯的惨烈战役中,他们主动请缨,组成敢死队。 那个曾捧着哥哥“守土”枪杆的瘸腿小兵,身背炸药,在枪林弹雨中第一个攀上城墙垛口。 叛军的长矛刺穿了他的胸膛,他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死死拽住敌军的旗帜,为后续战友撕开了一道用生命换来的缺口。 城下的老兵们目睹此景,发出震天的怒吼:“为弟兄们报仇!” 城破之后,左宗棠在断壁残垣间,找到了那半截浸透鲜血、变得暗红的枪杆。 他沉默良久,命人小心收好。 随后,他亲自主持,将在此役及多年坚守中牺牲的每一位老兵的名字,誊写在布帛上,并下令:“将这些名字,刻于玛纳斯城墙之上!让后世子孙铭记,是谁,将忠骨埋于此地,换回了这片山河!” 当有人议论左宗棠西征是为个人功名时,只需看看他如何抚摸老兵冻掉脚趾的残足,如何目睹他们将朝廷补发的微薄饷银悉数换成种子,撒播在刚刚收复、还弥漫着硝烟的土地上。 那一刻,所有的功名之论都显得苍白而可笑。 在清廷在朝堂之上“新疆无用,弃之可也”妥协时,正是这群衣衫褴褛的士兵和那位白发苍苍的统帅,向世人宣告:“国土,是祖先埋骨之所,是血脉中的家园,是值得用生命去守护的永恒疆域!“ 主要信源:(《清史稿·左宗棠传》金台资讯——兵饷粮运艰难万状|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4)、人民网——收复新疆 名垂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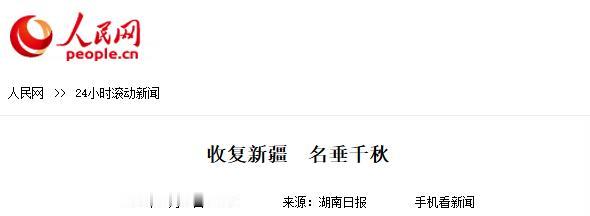

用户10xxx21
中华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