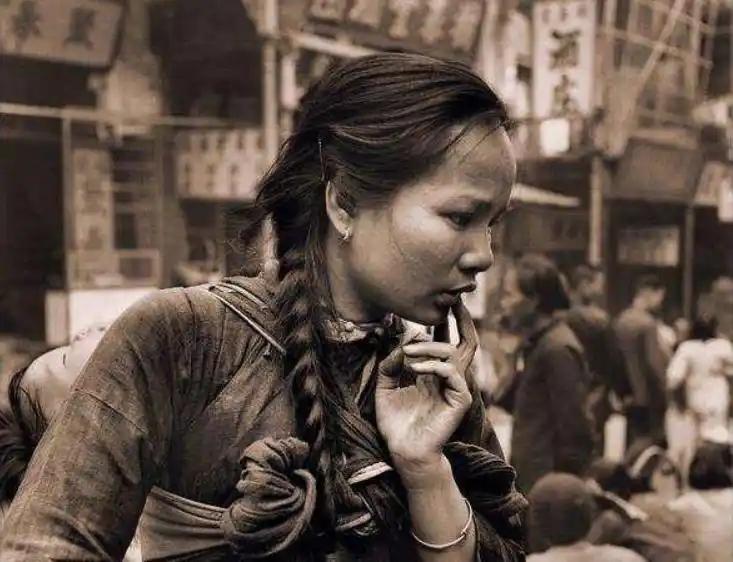1942年,地主杨大山为了讨日军欢心,在家里盛情款待。然而,酒足饭饱后的日军竟指着他怀孕两个月了的儿媳妇说:“她我要了!”杨大山赶紧跪地求饶…… 陕西马坊沟的夏天闷得人喘不过气,蝉鸣声撕扯着燥热的空气。地主杨大山站在青石台阶上,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 他抻了抻身上簇新的绸缎褂子,袖口用金线绣的"福"字在毒日头下晃得刺眼。 院子里摆开三张八仙桌,青花瓷盘里堆着酱牛肉、红烧鲤鱼,刚启封的酒坛飘出浓烈的香气,荤腥味混着酒气直往人鼻子里钻。 这个在马坊沟盘踞了三代的地主,平日里对佃户非打即骂,此刻却像热锅上的蚂蚁般焦躁。 远处传来皮靴踏地的闷响,三个穿黄呢子军装的日军军官跨进院门,领头的松本少佐肩章闪着冷光,腰间的佩刀随着步伐轻轻晃动。 杨大山瞬间弯下腰,脸上皱纹堆成朵蔫巴的菊花,连声招呼:"太君辛苦!快请上座!"他小跑着在前引路,绸缎褂子的后襟很快洇出深色汗渍。 酒过三巡,松本油乎乎的手拍打着杨大山的脸,金线绣的福字沾满油星。杨大山赔着笑,眼角却瞟向西厢房——见门帘纹丝不动,才暗自松了口气。 突然帘子一掀,杨大山的儿媳翠云端着醒酒汤出来。她穿着洗得发灰的月白衫子,乌黑的发髻斜插着婆婆留下的银簪。 五个月的身孕让她步履蹒跚,端着汤碗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席间霎时死寂,松本的酒杯"哐当"摔碎在青石板上,眼珠子死死黏在少妇微隆的肚子上。 杨大山像被针扎了似的弹起来,绸褂后背瞬间湿透。 两个日本兵饿狼般扑向翠云。“这个女人,我要了!” 银簪"叮当"落地,翠云被两个日本兵扑倒在地上,青丝散了一肩。 东厢房猛地冲出个抡扁担的后生——杨大山的独子铁柱赤着膊,扁担带着风声砸下。"八嘎!"刺刀扎进他胸膛时,血箭喷上杨大山前襟的金线福字,晕开朵朵暗梅。 翠云撕心裂肺的哭喊惊飞檐下家雀,杨大山疯魔般扑向松本,却被枪托砸得门牙崩落。 柴房腾起浓烟时,这个给日军送过三十八坛老酒、五十四只肥羊的汉奸,被捆在自己砍的槐木柴堆上。 火苗舔舐绸缎的焦糊味里,院外传来更多惨叫,日军点燃了整个杨宅,七个躲在地窖的长工全成了焦炭。松本狞笑着将火把扔进柴堆,火舌瞬间吞没杨大山圆瞪的双眼。 后来村民经过废墟,总见断梁间开着星星点点的野花。放羊老汉说像翠云鬓角坠落的银簪花,赶车后生说那是铁柱扁担沾的槐花。 孩子们常在焦黑的槐树桩前驻足,这棵烧得只剩半截的老树,第二年春竟从炭黑的树皮缝里钻出嫩芽,新抽的枝条亭亭如盖立在瓦砾堆上,像杆戳破青天的枪。 每逢清明,总有人往树洞里塞纸条。有张皱巴巴的草纸上歪扭写着:"爹,俺在山西打鬼子。"署名是当年逃出火海的小马倌。 山风吹过新槐的枝叶,沙沙声像极了那日翠云散落的青丝,也像地窖里长工们最后的呜咽。 这棵树成了无字的碑,年轮里刻着最朴素的道理:跪着求来的太平,终会被火焚尽;唯有挺直的脊梁,才能在焦土上长出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