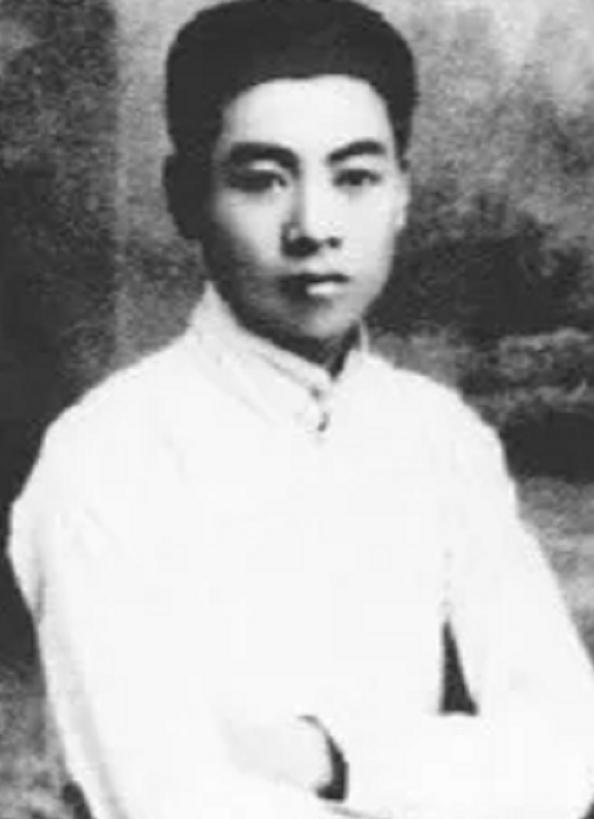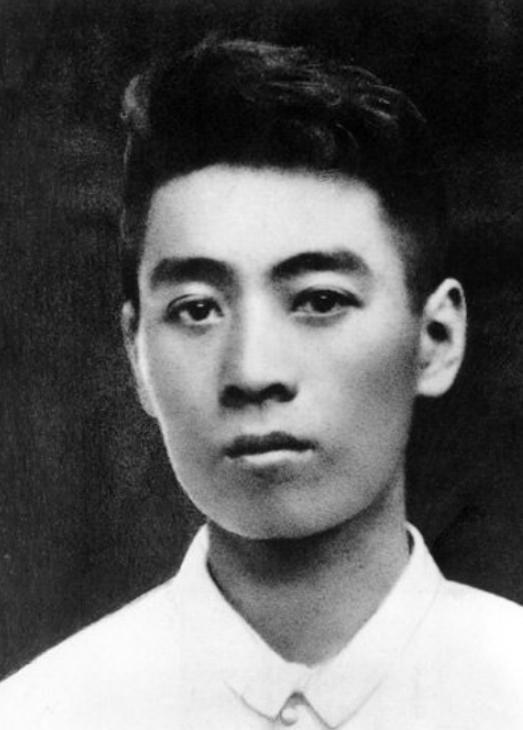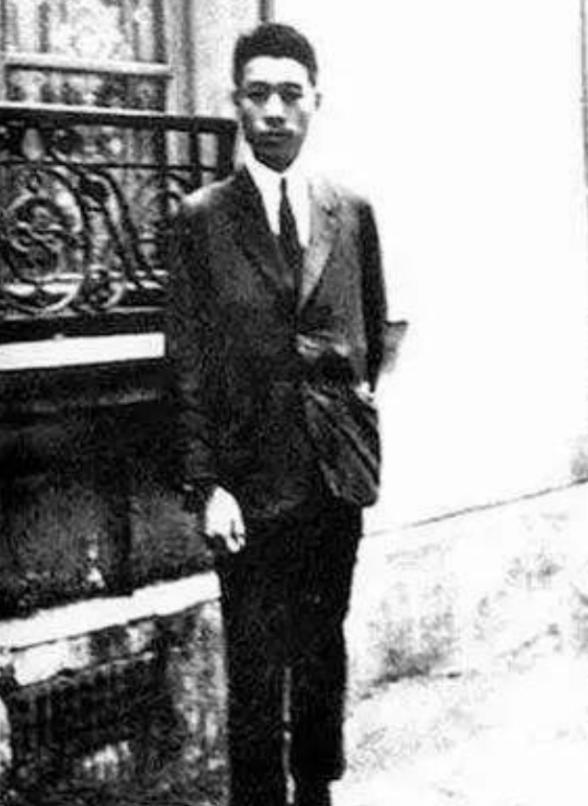55年周总理途径云南,见到曾经女友,周总理:这是小超的意思 “1955年4月8日早晨七点五十分,老陈,时间差不多了。”周恩来压低声音嘱咐身旁的陈方。四周静得只剩鸟鸣,省委招待所的小院里清风拂过,他整理了一下风衣下摆,转身迎向门口的张若名、杨堃夫妻。 周恩来此行的公开目的,是转道雅加达参加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真实行程却对外严密封锁。国民党特务刚刚在香港策划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失败,情报人员依旧不敢掉以轻心。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先在昆明停留半天,只因为邓颖超叮嘱:“一定要替我问问若名姐。” 距离上一次见面,已整整二十七年。握手瞬间,周恩来轻声问候:“旅途劳顿,你身体还好?”张若名微微颔首,眼角浮现细纹。气氛并不尴尬,反倒像久别的战友重逢。寒暄之后,大家落座,无人提及年轻时那段情感,谈论的仍是工作与学习。周恩来要她多读《毛泽东选集》,要杨堃配合学校在青年师生中推广普通话,“眼下最急的是打通西南和内地学术交流的脉络”,他强调。 时间拨回到1919年。那年五月,天津法租界外聚满学生,周恩来站在人群前端呼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响彻街头。台下张若名第一次认真审视这个江苏青年——身形瘦削,举手投足却有不容忽视的锐气。她原本性格刚烈,父亲续娶的阴影让她更早反抗封建。进了天津一女师,她和邓颖超、郭隆真组织“女界爱国同志会”,从此与周恩来在同一条战线上。 五四风潮后不久,“觉悟社”秘密成立。二十一位成员,男女各半,社训写着“精诚团结,牺牲小我”。在那个讲求“男女大防”的年代,这种并肩劳动、共同夜读的场景,本身就是宣言。张若名记得,社友曾半开玩笑起哄:“周舍长,你俩可要负责啊!”周恩来推推眼镜,回一句“革命要紧,其他免提”,众人哄笑收场。外人瞧来,他们像对情侣;自己心里却清楚,那是一种同志式依赖。 1920年初,两人同被捕入狱。潮湿牢房里,周恩来把《我的忏悔》和一迭诗稿交到隔墙的张若名手里:“万一我不在,替我保存。”张若名夜里点着油灯誊抄,指尖染上墨迹。绝食七天后,当局迫于舆论放人。学籍被开除,她干脆与家庭决裂,报名留法勤工俭学。 同年冬天,他们乘“亚丁号”邮轮抵马赛。巴黎寒风凛冽,青年们靠分送中文报纸、洗盘子维持生计。欧洲民主幻灭的落差,使周恩来彻底拥抱马克思主义。组织秘密会议常在凌晨两点举行,张若名法语流利,经常负责与法共通信。“她翻译《资本论》时通宵不眠。”周恩来后来对侄女周秉德回忆,“那个劲头我终生难忘。” 感情在此时水到渠成。一次塞纳河边散步,周恩来终于说出“我愿意与你并肩走到革命胜利”,张若名没回答,直接伸手握住了他。他们彼此配合,进步极快,可命运又一次拐弯。1924年,列宁追悼会事件让张若名被警方盯上,少共内部审查、意见分歧,给她沉重打击。她写信给周恩来:“我需要静一静。”周恩来再三挽留未果,二人终止恋情——不是因为感情淡,而是道路选择出现岔口。 周恩来返国,投身大革命。邓颖超从武汉来到上海协助工作,两人携手,于1925年广州简朴成婚。婚书用毛笔写着“革命伴侣”,没有花束,却有无数同志见证。与此同时,张若名留在里昂大学,攻读心理学、伦理学,终获博士学位。她在日记里写下一句法文:“Il faut vivre et avancer.”——必须活下去,并向前。 1928年夏,周恩来经过里昂,约她在郊外一家小咖啡馆。为了安全,他戴墨镜,进门时仍被张若名一眼认出。短暂交谈,内容多是国内形势,外加“邓颖超让我向你问好”。临别,周恩来说:“若名,请保重。”张若名笑答:“保管党的秘密,比保管我的学位证更重要。” 抗战爆发后,张若名回国,于云南大学任教。课堂上,她讲阶级分析,也教学生如何做田野调查。有人不解她为何远离政治中心,她只说“昆明需要老师”。1949年后,她继续执教,直到接到1955年那通电话。 回到招待所的客厅,周恩来看表,距起飞还有一个小时。他再次询问:“真不考虑去北京?”张若名摇头:“学生离不开我。”他点点头,不再劝。握手道别时,他把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报》放在桌上,“留作教学参考”。随后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下午三点,专机升空。机舱里,周恩来提笔写下一封信,收信人是邓颖超,内容只有一句:“若名姐一切安好。”信纸被折成方块,夹在公文包最前层。 昆明的暮色降临,张若名站在办公楼阳台,远望滇池水面,她并不知道特务再次策划的阴谋被挫败,也没料到这将是与周恩来最后一次握手。她只记得,他临行前轻声说的那句话——“这是小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