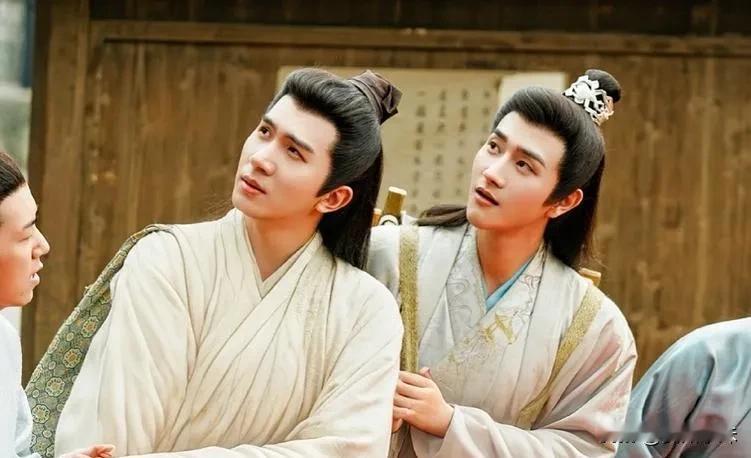东晋的时候,有一对兄弟俩,兄弟俩的父亲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小妾,两人终日里甜蜜有加,因此惹得兄弟俩的母亲嫉妒异常。 东晋那会儿,建康城里有个大佬级别的商人,名叫李询,外号“李半城”。这家伙起初是个推着油桶满街跑的小贩,后来入赘张家,靠着脑袋瓜子里的生意经,愣是把家业搞成了商业巨头。李询和张氏生了俩儿子,一个叫李钦,一个叫李错,按说这一家子该是其乐融融。可张氏年纪一大,颜值下滑,李询就开始对她爱答不理,反倒迷上了一个叫刘氏的小嫩妹,最后还把人娶进门做了小老婆。张氏一看,心里头那个憋屈啊,家里气氛一下就僵了。俩儿子心疼老妈,想给老妈出口气,结果这一闹,家里就炸了锅。 李询,五十出头,脑门上光溜溜的,就鬓角剩点头发,总爱用发油抹得锃亮。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从街头小贩混成“李半城”,可也最忌讳别人提他入赘的事。对张氏,他谈不上恨,就是腻了——当年娶她是为了张家的本钱,如今家业大了,就想找个能让他觉得自己还年轻的人。 张氏,比李询小两岁,年轻时也是建康城里数得着的美人,一手算盘打得比账房先生还精。只是这些年操持家业,眼角爬了皱纹,性子也躁了些。她恨的不是刘氏年轻,是李询忘了当初是谁把压箱底的银子拿出来给他囤货,是谁陪着他在雨夜里守着快要发霉的布匹。 李钦,二十三岁,跟着父亲打理铺子,性子随妈,稳当,就是认死理。他总记得小时候娘把最后一块糕点塞给他,爹却在旁边和账房喝酒,所以见不得娘受委屈。 李错,十九岁,还在学堂念书,脾气像炮仗,一点就炸。他觉得爹就是陈世美,刘氏就是狐狸精,好几次在饭桌上想拍桌子,都被哥哥按住了。 刘氏,才十七,是乡下人家的女儿,爹欠了李询的银子,把她送来抵债的。她模样是真俊,眼尾有点往上挑,笑起来俩酒窝,可胆子小,见了张氏就发抖,见了李询也只会低着头说“听老爷的”。 最先忍不住的是李错。 那天李询给刘氏买了支金步摇,插在发髻上,吃饭时还一个劲儿给她夹菜,张氏的筷子在碗里戳得“当当”响。 夜里,李错揣着块石头,摸到刘氏住的小院,想把那扇雕花木窗砸了,出出恶气。刚举起手,就被李钦拽住了。 “你疯了?”李钦压低声音,“砸了窗户,爹只会更护着她,娘更难受。” “那咋办?就看着娘天天抹眼泪?”李错挣开他的手,眼眶通红。 李钦没说话,他在想别的招。 转天,李钦去布庄查账,故意把刘氏陪嫁的那匹云锦记成了“库房损耗”。李询对账时发现了,皱着眉问:“这云锦呢?” 李钦头也不抬:“前儿见娘的披风旧了,给娘改了件新的。” 李询没发作,心里却不痛快——那是他特意托人从蜀地带来的,想给刘氏做件新衣裳。 张氏知道了,摸着身上软乎乎的披风,眼圈红了,却骂儿子:“胡闹!那是你爹给刘姨娘的。”嘴上骂着,嘴角却绷不住往上翘。 可这招没用多久。 李询干脆把刘氏的小院加了道锁,钥匙就挂在自己腰上,连张氏的贴身丫鬟都不许靠近。还让厨房每天给刘氏炖燕窝,张氏的燕窝却换成了银耳。 李错又炸了,趁李询去外地进货,带着几个相熟的泼皮,堵在刘氏小院门口骂街,什么“狐狸精”“不要脸”,骂得最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刘氏吓得缩在屋里哭,张氏听见了,跑到门口想拦,却被李错怼回来:“娘!您还护着她?” 张氏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她心里解气,又觉得这场景实在难看。 等李询回来,刘氏扑在他怀里哭,头发乱了,金步摇也掉了。李询一看就火了,抓起藤条就去找俩儿子。 李错梗着脖子不认错,李钦却“扑通”跪下了:“爹,是我让弟弟去的。您要是气不过,就打我吧。” 李询的藤条举在半空,落不下去。他看着大儿子背上的伤——那是去年帮他挡劫匪时被砍的,又看看小儿子倔强的脸,突然觉得累得慌。 “你们俩……”他叹了口气,把藤条扔在地上,“从今天起,家里的事,你们别管了。” 这话像盆冷水,浇得兄弟俩心都凉了。 更糟的还在后头。 张氏见儿子替自己出头反倒挨了训,心里堵得慌,没过俩月就病倒了,咳得直不起腰。李询请了郎中,开了方子,却没怎么来看过。 刘氏倒是来过一次,端着碗燕窝,刚进门就被张氏泼了一身:“滚!别用你的脏东西恶心我!” 刘氏吓得哭着跑了,从此再没踏足张氏的院子。 李钦守在母亲床边,看着她一天比一天瘦,心里像被猫抓。他去找李询,磕了三个头:“爹,娘快不行了,您去看看她吧。当年您在码头被人抢了货,是娘跪着求我外公借的银子;您生天花,是娘守了您七天七夜没合眼……” 李询背对着他,肩膀动了动,没回头。 没过多久,张氏就走了。 出殡那天,李询穿着素服,站在灵前,眼神空落落的。李错没理他,李钦给父亲磕了个头,声音哑得厉害:“爹,娘到死都没说过您一句坏话。” 信息来源:参考东晋《世说新语》中类似家庭记载及民间故事整理